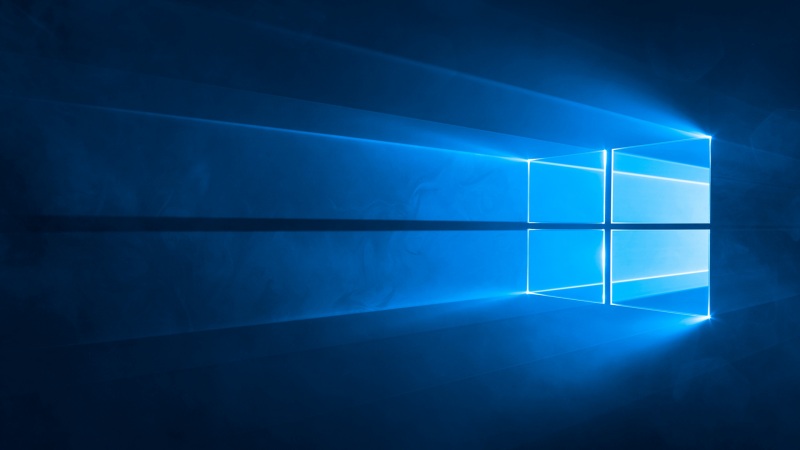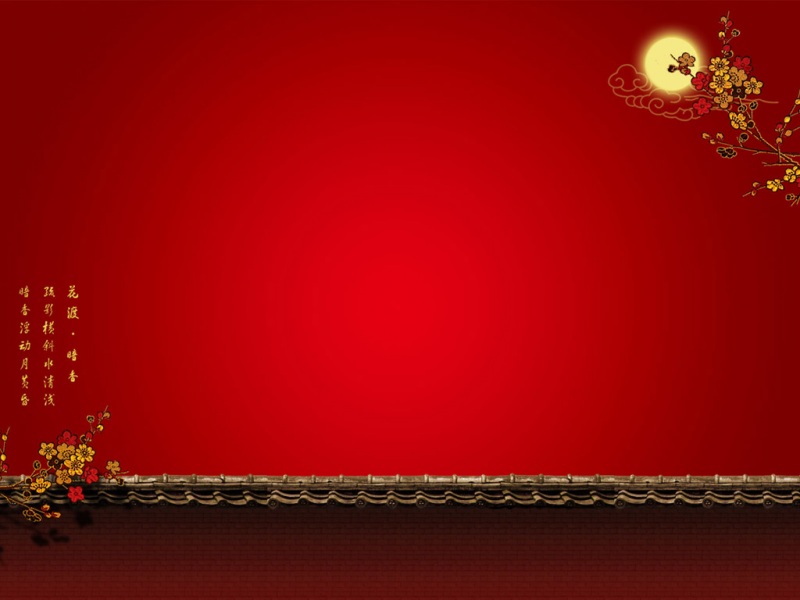提示:本文共有 7979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16 分钟。
奶奶的麸子酱
木 木
(文长7970字,读完约需30分钟)
史铁生《奶奶的星星》:我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蜡烛……
一
打我记事起,奶奶是极少做麸子酱的。一是次数少,二是量少。在槐花桐花枣花的清香中,如果能有一股浓郁的酱香直钻心肺,那就是我最幸福的春天。
夹着奶奶新做好的麸子酱,我能多吃好几个馒头。可是,每次我偷偷吃了奶奶做的好吃的,回家总会挨我爸吵。我爸舍不得让我吃掉奶奶辛苦做出来的饭菜;因为奶奶的右胳膊是残疾的,只能抬到腰际,做饭依靠的是左手。
胳膊残疾是因为餐风宿露加急性乳腺炎。寒冬腊月,我奶奶生下她最小的儿子,转头就砸碎了河冰洗洗涮涮。熬到来年春天,青黄不接,只得扔下儿子,漫地里去刨被遗落在黄土里的一切可以吞进肚里的东西。来不及喂儿子的奶,积聚,发炎;常日的风霜雨寒,饥饿劳累,让胳膊日渐肿胀,最后长成一个大脓包,只得求医剜了一刀,从此右胳膊再也不能正常举起。
那时候的奶奶,和我如今的年龄一样,正值壮年。
那时候的奶奶,刚刚挖完河没两年。
挖河的苦,听村里老人说,一般的男人也吃不消,都是挑村里的壮劳力,且专门让他们吃稠饭,才能支撑下来。村里按户摊派,一户出一个男劳力。到我奶奶家时,望着屋里高矮不一却齐声喊“饿”的孩子,想想队长说的挖一天河给半碗黄豆,我奶奶咬咬牙,自己去了。
我从小学到高中,从村子到镇上到县城,求学路上一直走的那条宽阔县道,两旁绿杨成荫;那又宽又高的路基,就是我奶奶和那些男人们一锨一锨挖起,一筐一筐抬上去,一层一层垫起来的。
那会儿正轰轰烈烈搞合作社合食堂,我爷爷被抽调到乡上的机械厂,大炼钢铁去了。全村一切含铁的东西都被搜出来,送到了乡里的钢铁炉。全村的铁锅,一口一口在打麦场上整整齐齐排好队,被队长挨个儿敲破。我奶奶还没来得及把挖河挣来的豆子给孩子们煮完,就得了伤寒病倒下了,搜东西的人进来时,她顺手在被子下藏了一个搪瓷尿盆,以期夜深人静的时候给她仅存一口气的二儿子煮点菜粥。那个盆儿还是被人翻出来,一手甩进了粪坑里。
天灾人祸,洪水泛滥,颗粒无收,院里的老榆树也迟迟不再发芽。我奶奶只得同意把她仅存一口气的二儿子送人,以求活命。儿子被送走之后,奶奶又后悔了。她下了床,一只手拄着拐棍,淌着大水,去找儿子;到了一看,儿子正抱着一块饼子一跳一跳吃得香。我奶奶一把搂过儿子,大哭“儿啊,咱娘俩饿死到一块儿吧……”
这个被背回来的儿子,就是我爸。
二
我奶奶1926年正月十七出生,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可那又如何?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朝不保夕的时候,唯一的女儿也不会得到额外的照顾。不是不想,是有心无力。我奶奶就如田间地头的野草,不知不觉蓬蓬勃勃长大,嫁人。父母到底不舍得唯一的女儿远嫁,于是嫁给了一沟之隔的邻村,我爷爷。
我爷爷家更穷。祖上没有一分土地,兄弟五个,一个姐姐。我老爷爷是锄二八地的,连个长工都不算,就是一个给地主家打杂的临时工,等到秋收,主家收走八分,我老爷爷拎走少得可怜的二分,来养活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结婚,分家。我爷爷奶奶只分到了一个腌菜缸和一只豁口碗,不是大号的,也没有筷子。
唯一的欣慰是,我奶奶遇到的公公婆婆,为人还不错。我老爷爷是方圆几里有名的懂礼之人。我老奶奶娘家原是翰林院人,可惜母亲早逝,她四岁那年抽大烟的父亲也撇下她,撒手西去。
关于老奶奶,我脑子里一直刻着两幅画。
一幅是我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的暖阳下,和老奶奶一起剥玉米籽,我一颗一颗抠,她拿起来两个玉米棒子,凑一起一拧一划拉就是三四行,她一边划拉一边笑眯眯和我说:“你这是读书写字的手。”另一幅是挺冷的一个早晨,我起得特别早,我爷爷抱着她尿湿的床单去河里洗了,我姑奶奶和奶奶一起去做她要喝的面疙瘩汤了,我一个人蹲在她床边玩。过了会儿姑奶奶端着汤过来喊“娘,起来喝汤了。”我老奶奶却像睡着了一样,无疾而终。后来,大家都说我是个有福气之人,得了老奶奶的“济”。
我太奶奶,虽说她自出生就没享受到一天家族的荣华,反而受尽颠沛穷困之苦,但是她知道读书有用,曾经咬紧牙关供我爷爷读了两年私塾,后来实在没粮食念书了,就让我爷爷跟着一个养羊的外乡人学唱戏,学会了就对着戏词看,继续认了一些字,知道了和现实凄苦不一样的另一个世界,那世界里郎情妾意,快意恩仇。
就是这个读书认字的决定,成就了我奶奶的幸福,也毁了我奶奶的幸福。
三
我奶奶是填房,一辈子都生活在前任的阴影之下。前任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作为晚辈无从知晓,但是每到节日,就见爷爷去她的坟前烧纸祭拜,想必是和我奶奶不一样的。后来断断续续听村里老人讲,我奶奶的前任是个地主家的闺女,知书达理,性格温婉,可惜嫁过来没多久就生病去世了。了然,对于爱唱戏爱了一辈子的爷爷来说,这戏词中才有的女子,又止于初见的美好,绝对是胸口的一颗朱砂痣啊。
同为女人的我奶奶,不爱笑,寡言少语,不断文认字,不懂戏词风月,每天除了发愁怎么揭开锅有饭给孩子们吃,就是埋头苦干,偏偏干活速度又慢。村里人说,我奶奶给队里干活时候,别人干活她在干,别人歇着她在干,别人吃饭她在干,别人睡着了她还在干,就这,才能和别人赶齐头,挣差不多的公分。村里人说这件事的口吻,是嘲笑的。
我邻居不止一个把我奶奶卖箔的事儿当笑话讲:青高粱杆子刚编好的箔,傻沉,四婶儿(我爷爷排行老四)扛了二十里路去集上卖。就因为人家非要少给一毛钱,几十里的路,她又原封不动扛回来。你说傻不傻?一天没吃饭,扛着沉不沉?扛那么远,不累?没卖上钱,孩子吃啥?
不爱说话的人,往往性格执拗,活成旁人眼中的傻子。当妯娌把尿盆、淘草水泼在她门前时,她亦是一声不吭;她知道,她吭声也没用。再后来,茅草房顶破的不能住了,她带着一家人扒了旧房重新盖的时候,后院的人不愿意,非说她压了他们向外的出路,三间的房子扒了只盖成两间半,她依然忍下了。
从我记事起,我就觉得我奶奶活得太憋屈了,从不大声说话,从不发怒,我把她珍藏的袜子用剪子剪了,她只是叹口气;我有次睡觉做梦,一脚把她从床上踹了下去,她走路瘸了好几天,也忍着不吵我。
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婚姻,在外人眼中,也是典型的憋屈。如果正在做着饭,突然听到街上有人大声喧哗,我奶奶的左手就发抖,央告我“你去看看是不是你爷跟人吵架了”。我爷爷回到家吹胡子瞪眼,我奶奶整天做好饭等着我爷爷说“吃饭”才敢揭开锅盖。
有次我爷爷拿着孩子们辛苦摘桑养蚕结出的茧去集上卖,换粮食。换到钱的那一刻,他突然改变了决定,买了几个瓜,站在集市头上豪爽地甩开腮帮子,吃完,唱着戏,空着手,回家。所有人像嘲笑我奶奶那样嘲笑我爷爷。可我奶奶,看着他空着的双手,一句话也没说,流着泪煮了一锅菜叶子给他们的孩子填肚子。
故事里的事,终究抵不过现实的凄苦。沉浸在故事里的人,总归要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我奶奶虽然不识字,却早就在生活的压榨下明白了这个理儿;我爷爷,在只能天天顿顿捧着一团菜叶子的时候,才醒悟了。
我爷爷借了粮食蒸馒头卖,磨下来的麸子也卖。我奶奶就把从石磨缝隙里扫出来的麸子渣渣,蒸了,捂起来让它发烧,然后放太阳下晒,晒晒搅搅,晒成棕褐色的麸子酱,酱香扑鼻。
我奶奶就这样,用尽心力,把寡淡粗粝的生活残渣,收集起来,酿出了香气。
四
很快,新的运动来临,粮食买不到了,馒头也卖不成了。我奶奶的麸子酱,自然也就做不成了。随着麸子酱的香味儿一起散去的,还有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为了填饱肚子,每个人都是竭尽全力,再也无暇顾及他人,哪怕是自己亲爹娘、亲儿女。本是同根,却远不及一个陌生人。
太阳升起的清晨,总会有噩耗,有的人饿死,有的人撑死。
1959年的春天,我爷爷饿得只剩眼珠子会动时被抬进了医院,葛医生只看了一眼就让“抬回家等着吧”,临了又追出来加一句:“回去灌点面水试试吧。”驻村工作队里一位见惯生死的干部老杨,走路虎虎生风,巡视一圈后指着我爷爷:“他这么年轻,饿死了可惜,就尽着他吃吧。”
我奶奶就每天去大食堂领面水,小心翼翼地捧回来,喂了我爷爷。再用唯一的瓦罐去打全家人的饭。一开始是一次喂两口,一点点增加,到一合碗、一小盆。村食堂那个做饭的妇女,看我爷爷会爬了,果断地断了我爷爷的面水。根本没有恢复吞咽“洋火盒”黑饼子的我爷爷,有幸赶上了麦子灌浆,他就每天爬到刚刚灌浆的麦田里,揉了满是汁液的青麦籽,吞下去。
麦子成熟,风吹麦浪,一望金黄。我爷爷这个土地上的庄稼汉,坐在麦田里突然有了力量,站了起来,捡回了一条命。
我爷爷自始至终,没有往家带过一颗青麦籽;我奶奶也从未要过,“队里的东西,咋能吃了还拿啊,都挨饿啊。”往后的无数年,我爷爷奶奶一直打听那个工作队的老杨,可是毫无音讯,这个人就像从未来过一样。
1960年,我爷爷又一次拾起他的故事,只不过,这次是带着他戏里的故事和他的大儿子,背井离乡,去讨饭,一走三年无音讯。
我奶奶一个人带着余下的儿女,留在家里,吃糠咽菜。除夕的年夜饭、年初一的饺子,都是一团连盐巴也没有的黑红薯叶子。
1963年,洪水逐渐褪去,春暖花未开,村头的树皮和地里的野菜根,也全进了人的肚子。村里开始允许一人借队里一分盐碱地,生产自救。在我爸把他棉裤里的棉花掏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我爷爷终于带着我大伯出现在了村头。成麻袋的馍馍头儿铺在床上,我奶奶一遍又一遍抚摸着那一块块颜色各异、大小不一的馍馍头儿时,有的上面还带着参差不齐的牙印儿,哭得不能自已。
我奶奶虽然拖着残废的胳膊背回了一个送出去的儿子,可是依然没有能力阻止痛苦的侵袭。她的大儿子,小小年纪逃荒要饭,未及成年便远走他乡,像断线的风筝,多次出生入死;她天天看着背回来的二儿子“饿,饿,饿”地哭,把手指唆得通红;她还有一个儿子,在她出门干农活的时候,在家发烧烧死了;她的小女儿,也是发烧,她着急忙慌去请医生,一针下去,小女儿耳朵聋了……
这些,她依然忍下,咽了下去。
五
熬过了一年再熬四季,院里的老榆树,一遍一遍被扒皮,竟然没有死,依然枝繁叶茂;我奶奶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也都逐渐长大。
眼看着大儿子到了到了定亲成家的年龄,望着四面透风,头顶透亮的破房子,我奶奶哭着同意了他的大儿子又一次背井离乡。
1964年的春天,冷得出奇,本该春暖花开的日子,下起了琉璃(冻雨),她17岁的大儿子,穿着夹衣单鞋,踩着冰溜溜的黄土路,背着一卷没有布套的破棉絮,又一次离开了她的视线,跟着本家一位部队转业的兄长,去遥远的西北做建设。
车到乌鲁木齐,我大伯告别兄长,钻进蒙着帆布的大卡车里,摇摇晃晃前行,六七天之后,到了一个叫阿耳泰可可托海的深山中,进入地下,修水电站。这些,都是我奶奶听人读了来信得知的;在后来无数个星星闪亮的夜晚,她摇着蒲扇,一遍一遍讲给我听。
1965年的冬天,可可托海的温度达到零下五十七度,我大伯的信突然断了。我奶奶就是那时候,在一个个睡不着的深夜,学会了抽烟。几个月后我大伯的信恢复,只说是扛木头摔断了腿,已经好了。1967年的秋天,突然动乱,我大伯的信又一次断了;1969年转去辉铜矿之后,我大伯的信又断了,因为胳膊卷进了传送带;1974年搬到铅锌矿,我大伯的信又断了……
每一次信的突然中断,都是我奶奶拼命抽烟的时候。一个个深夜,她不说话,只有烟头明明灭灭,一根接一根。
家里没有多余的钱来买烟,我奶奶白天出去干活的时候,就一边走一边捡别人吸过的烟头,回家仔细剥开,把烟丝归拢,再用黄裱纸把烟丝卷成一个卷,点着了吸;捡不到烟头的时候,她就直接卷叶子。这个习惯,一直到我记事到我上小学,那时候的我,以帮她捡烟头、剥烟头为乐趣……
我奶奶终于忍不下去了,喊出她刚满17岁的二儿子,递给他一个地址只到县级的信封,让他去寻找她的大儿子。她的两个儿子,都是在17岁这年,第一次坐火车,远赴一个未知的地方。兄弟俩终于在人群中遇见的时刻,她的大儿子刚刚能拄着拐棍下地行走。母子连心,她大儿子的脚被砸断了。
六
1981年分地单干以后,院子里的老榆树彻底完成了它救人于饥荒的使命,化为了屋顶和家具上的一块块木板。我奶奶一直对我老奶奶“读书认字”的信念深信不疑,无论饿成什么样子,只要学校还在,她都坚持送她的孩子去学堂。
彼时,我大伯成了稳定的矿工,我爸我叔都相继考上了大学,我爷爷开始做他最看不中的手艺——扎纸活。一座座色彩艳丽的亭台楼阁,在我爷爷的手下出现,又一次次在他人的坟前,化为灰烬。我爷爷少年时代读的那些故事,大约都化在了这一次次的扎制之中;换来的钱,给我买烧饼吃。
日子逐渐好过起来,我奶奶开始继续做麸子酱。
我蹲在院子里的阴凉下,看奶奶用她的左胳膊,一遍一遍搅合她的麸子酱,她一边搅一边告诉我,每一步该怎么做;还告诉我,麸子酱不能见一丁点儿雨水,只要落进一滴,绝对坏掉,晒酱的时候,得时刻提防变天。一遇到天色不定,我奶奶就颠着她放开的小脚,赶着去搬麸子酱。
她一边做麸子酱,一边催我读书。点着煤油灯的冬夜,我装模作样拿一本看图识字,依偎在她身边,偷偷看她缝衣服做鞋;她常常一边扎针一边问我,“你爸回来了没有?”“你爸啥时候走?”一遍又一遍。我就一遍又一遍回答“回来了,明天天明走。”那时候,我爸在镇上教书,是距离她最近的儿子。我小叔和我大伯,一年或者两三年,才能回来一次。
大年初一的凌晨,我奶奶一定会早早把我喊起来,让我大声读书——“大年初一读书能考上状元,你老奶奶说的。”
我爷爷和我奶奶不同,他不催我读书,他说:“我家的孙子孙女,个个都是状元。”他教我用农具,收种庄稼,种菜,盘瓜,煮汤,炒菜,蒸馒头……他常常袖着手,站在一边指挥我做,做错了也不恼,说下次就会了。
我爷爷和我奶奶,过着过着就颠倒了个个儿:我爷爷好像忘记了他读书的少年时光,着急忙慌教我和弟弟农人该会的一切;我奶奶,则坚定地要让我们走读书的路。
七
我奶奶在北京迎接了她最小的孙女之后,又转去了甘肃,和她大儿子一家团聚。我们都很高兴,认为奶奶终于熬得苦尽甘来,要享福了。准备送奶奶出门走的前几天,全家齐动手,给我奶奶剪头发的、洗衣服的、做好吃的、收拾行李的……帮不上忙的小孩子,就兴高采烈地转悠,各个喜气洋洋,比自己出门旅行还高兴。
住到临近麦收,我奶奶逐渐吃饭很少,想回家。我大伯大妈想着我奶奶一辈子离不开她的麦子,就赶在麦芒满天飞的时候,送她回了老家。回了老家的奶奶,一天也不耽搁,就加入我们抢收麦子的繁忙中。只是,她走路日益蹒跚,吃饭越来越少,问她,她只说天热农忙,累的。
颗粒归仓,玉米点上。我爸开着拖拉机把她拉到县医院,医生掀开她的衣襟只看了一眼,就摇了头。我奶奶的乳房,早已乌黑;我奶奶的癌细胞,早已扩散。她一直一直拖着,不肯告诉任何人,如果不是最后她实在咽不下饭菜,瘦得迅速,恐怕还会一直隐藏下去。
她隐忍了一辈子,沉默了一辈子,咽下去所有的辛苦和委屈。那些我们看不到听不到的苦痛,最后都反噬了她的身体。
1995年的夏天,酷暑炎热,可是我们全家,如坠冰窖。全家一如既往地团结,出钱出力,请最长的假,做最精细好吃的饭菜,找最好的药……我们喂她吃药时,都告诉她“这是胃药,吃了很快就能吃饭了”,我奶奶也总是很配合地咽下去,特别安静。
我从半岁开始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我奶奶熬了小米油,一口一口把我喂到会吃饭;我爷爷每两天去一次集市,买了烧饼回来,他俩嚼碎了喂我。如果我爸我妈训了我,我奶奶总是摸着我的头叹气,我爷爷总是瞪起他的大眼睛“光收拾小孩啥本事!”我上小学,在镇上,一周才能回家一次,第二天我就坐在教室里哭,我老师问我哭啥?我说“我想奶奶”,全班哄堂大笑。
我很害怕她突然死去,一周的中间总会骑车二十里跑回去看她一次,在她面前又总也忍不住掉泪,我爸就会瞪我,不让我靠近。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她能活得长一点,长一点,再长一点。她才刚刚69岁,还未来得及在生活的残酷之下喘均匀一口气,病魔就又缠上了她。
秋去冬来,她本来满头乌黑的头发已花白点点,她的疼痛一日多过一日,每次见她佝偻起瘦小的身体,我姑我爸就在旁边说“娘,你要是疼就喊出来”,她总是说“不咋疼”。终于在无数次忍耐之后,她长叹一声“谁的病谁知道,你们也别费那钱了。”
我的奶奶,熬到了1996年的二月,整70岁。临去世,她陷入昏迷时喊了两遍我大伯的名字,等她清醒过来,我爸问她“娘,你是不是想我大哥了,我给他发电报了,他马上就到家。”我奶奶仍是忍着,只说“我那是喊你弟哩,不是喊你哥。”我奶奶终究没有等到她那个从小就背井离乡的儿子踏进家门,就停止了呼吸。
从此,我的世界里再也没有麸子酱。
八
我奶奶去世后,当初拒绝了留在城市的我爸,迅速调进了县城,并带走了我们姐弟,让我们有了较为稳定的学习环境,把我们一个个送进了大学,应了当年讨饭人站在我奶奶门口唱的“一家三门大学生”。
我奶奶去世三周年,我爷爷重新捡起来被他扔了许久的手艺,用了一整个冬天,给我奶奶扎了全套的纸活,烧了。从此再不碰纸活。
我奶奶病重的那段时间,我爷爷又捡起了他曾经的故事,一日日坐在村头的树荫下,抱着收音机,听戏,唱戏,讲故事。村里人一边感慨着我奶奶一辈子不容易,一边听着我爷爷讲故事唱戏,一边扭头说我爷爷心狠。那时候,我沉浸在即将失去奶奶的巨大恐惧之中,也一度怨恨爷爷的狠心,尤其是看到村里人绘声绘色地讲述我爷爷说“还不如早点走了”的时候。
我奶奶去世之后,我爷爷突然很怕死,有一点点小毛病就大呼小叫,让所有人都陪着他;等到我小叔回家,他没有病也要让我小叔和我爸拉着他去县医院,告诉医生哪儿哪儿都疼,要吃药要打针要住院。等医生开了一堆补药回来,放在抽屉里直到长毛也不见他吃一次。
他放出话来:“我一定要活过你三奶奶,替你奶奶出口气。”彼时,我们晚辈早已放下芥蒂,亲如一家。我爷爷也是对所有的晚辈视如己出,甚至每到周末就搬个凳子坐到县高中的教学楼下,只为了看我三奶奶的孙子一眼,说几句话;可是对于活多久这件事,他始终咬着一口气不放松。他看着一个个年轻时强横的人晚年都不如他,就又拉了一群闲着无事的人,每日在他院子里拉着弦子唱戏,好不痛快!全家人对他既头疼又无奈。
等我毕业工作、结婚生子,我慢慢理解了爷爷最后一段时光的反常。奶奶走了,这世上,从此再也没了把他当成读书人宠着崇拜着的人,再也没了把他放在心尖尖上疼爱着人,再也没了总是无条件支持他的人;这世上,也从此再也没了忍受不完的委屈,再也没了吃不完的苦、咽不完的痛、抽不完的烟头……
我爷爷,他疯狂唱戏的背后,是无边无际的落寞,深入骨髓。
我三奶奶去世的第二年,我爷爷没有遗憾地走了,88岁。走之前,他已经忘记了这世上绝大多数的人和事,忘记了这世界给他的悲和喜;只记得他童年的玩伴,还有《百家姓》《三字经》……
刚生完女儿的夏天,我接到了爷爷去世的消息。那天,距离我的生日还有六天;小时候,每逢生日,爷爷在我头上“滚蛋”的时光仿佛还在昨天;想起我结婚时,爷爷一个人端坐着等我和土司跪拜的情景,何其孤单!虽然对爷爷的离去早有心理准备,我还是哭得止不住:这世上,我从此再也没了来自祖辈的关爱。
送我爷爷入土的时候,家里人没有送奶奶走的时候那么撕心裂肺。我爷爷终于赌赢了一口气,替我奶奶看到了她的儿女个个安家立业,衣食无忧,家庭幸福;孙子辈,一个个品学兼优,学业有成,连最小的孙女也已进入大学。我爷爷带着胜利的微笑去那边告知奶奶了。
那些年,我奶奶做麸子酱,我爷爷批评我奶奶“总是吃那些不中用的,白馍不好吃么?”的时候,也是带着这种胜利的微笑。
后记: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想着要把我奶奶的一生写下来,可是过了很多很多年,我还是提起笔就流泪。后来读史铁生《奶奶的星星》:我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蜡烛……我懂了。我奶奶已把苦涩粗粝,全酿成醇香,给了我们。我终于能擦干眼泪,记下来。
记下回忆,留下怀想: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奶奶的麸子酱|随心随笔”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