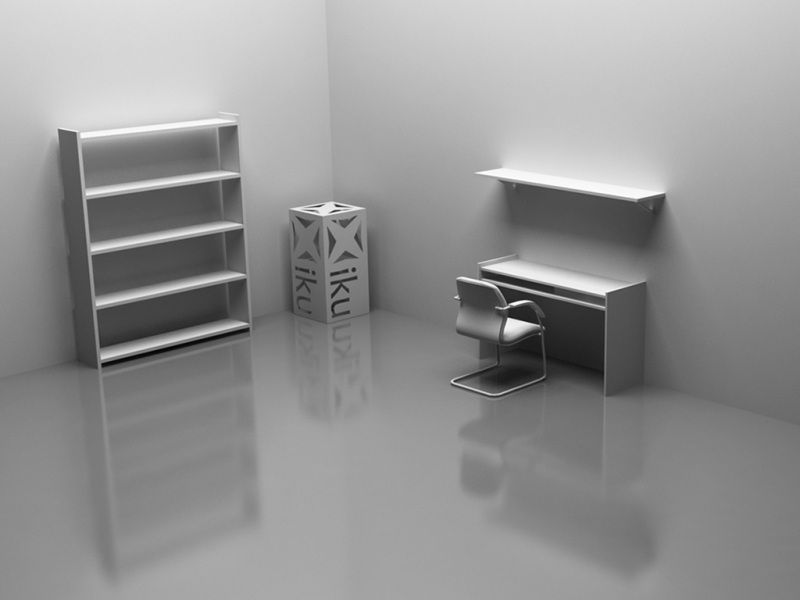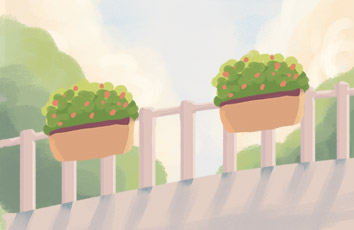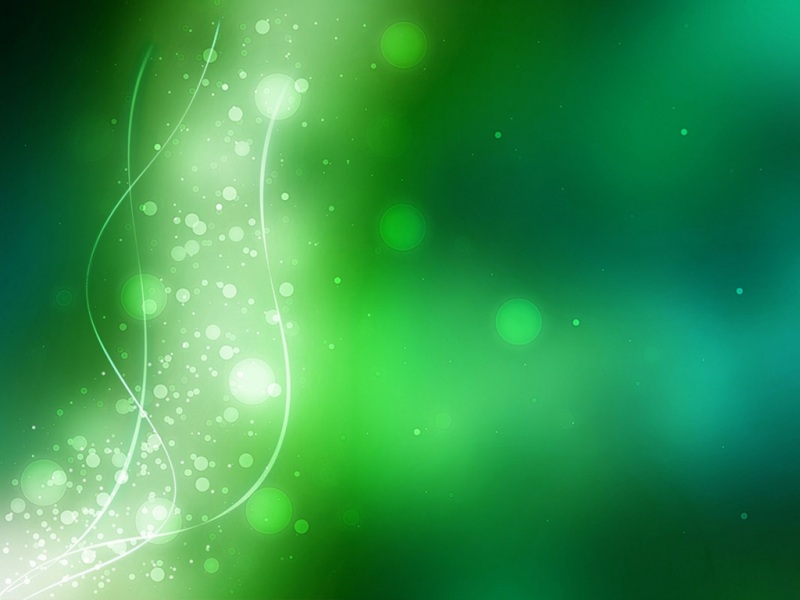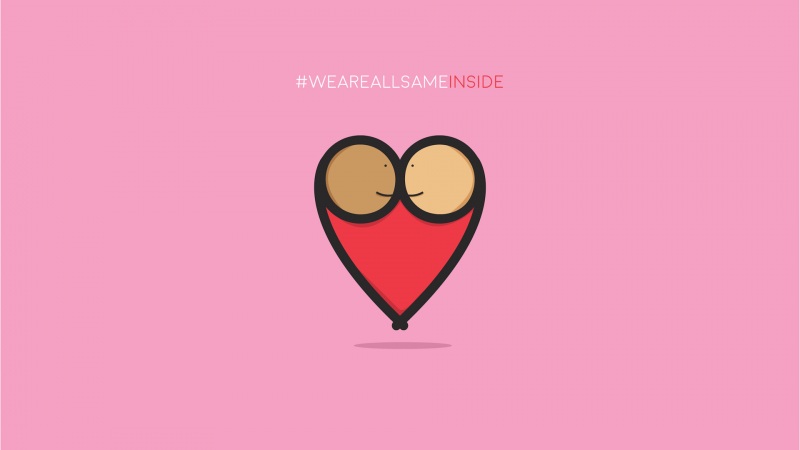提示:本文共有 13642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28 分钟。
20世纪80年代中国摇滚乐的诞生,首先应该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它契合了那个时代的特定需求,传达并疏导着一大批青年人特定的文化心理,是特定时期的文化产物,故与当时出现的众多文化事件有着精神层面的契合点。
下文通过对摇滚乐歌手张楚的《姐姐》进行个案分析,关涉这首歌曲背后所折射的普通社会个体的情感状态,并在诸多文化事件中探寻当时社会大众的群体感受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历史关联性。下文选自近期出版的《文化研究·第35辑》
(周宪、陶东风主编)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本文原标题为“弑父、青春、欲望:20世纪80年代文化众象的情态表征”,文章选自近期出版的《文化研究·第35辑》(周宪、陶东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原文作者 | 刘海
整理 | 吴鑫
返回一个特定年代的集体记忆,是当前关于“文化记忆”最时髦的话题,无论是在史学界、文学界,还是在影视艺术界。追随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遗产,法国第一代“年鉴派”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开辟的富有创造性的心态史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
以布洛赫和费弗尔为代表的第一代“年鉴派”的心态史研究,体现了“年鉴派”所坚持的一度被视为“异端”的研究兴趣,尤其是它通过“从想象、群体心理学和文化角度出发”对社会上的某些现象或问题给予的关注与研究的思维、理念及方法。在这一点上,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达成了一种默契,尤其是文化研究中对“文化记忆”的关注,无疑与年鉴学派“回归历史语境的特定心态”有着必然的牵连。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通过对摇滚乐歌手张楚的《姐姐》进行个案分析,关涉这首歌曲背后所折射的普通社会个体的情感状态,并在诸多文化事象中探寻当时社会大众的群体感受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历史关联性。
20世纪80年代末期,摇滚乐歌手张楚以一首《姐姐》迅急蜚声摇滚乐坛,并为众多摇滚歌迷所铭记,这首《姐姐》成为永恒的经典。一首歌曲或一张专辑,它的流行代表的不只是一个歌手的心声,而且是一个时代的共鸣。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个复杂的筛选程序,不可否认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一种集体情感给予的积极回应。或许,这种集体的回应中必然夹裹着潜在的、细微的个体性差异,但基于特定时代的集体性诉求构成了音乐旋律中的主导性音符,进而将它推向时代舞台的核心区域。
故此,我们并不是要讲述一个感伤的爱情故事,也不是追叙一个歌手的特定记忆,抑或一个年代的特定印记,而是要以此为契机,在“80年代”的历史基础上,回顾一个集体神话如何在特定条件下,由无数个别的“欲望的象征”构筑起关于那个特定年代的“集体记忆”,进而梳理那个时代的历史逻辑。
标志:反叛与弑父情结
关于“某个时代”或“某个年代”的特定记忆,有些人更认同某种特定理念的阐释与知识学的概念建构,而忽略了对历史现场的还原与挖掘。例如,20世纪的“80年代”,关于这个特定年代的历史记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在一种浪漫化、理想化抑或经典化的“前见”中,围绕这样的信念堆砌相关材料。而法国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却为我们重返历史的现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与方法,它旨在通过对心态史学观念与方法的梳理和使用,为我们返回历史的发生地创造一种新的路径。
仅就时代而言,“80年代”确实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代,它将中国生产力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氛围中解放出来,并且赋予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一种开放与改革的“大视野”。所以,在近十几年的“80年代怀旧热”中,更多地聚集了一批思想文化领域的学者。当然,那些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因为中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变革,如今已经成为政界要员、商业精英、大学教授、知名学者、著名文艺家、影像媒体的掌舵者等,80年代改变了这一代生于“50年代”的人的生活与命运,在他们集体性的怀旧与诗意的“青春还乡”情绪作用下,“80年代”无疑彻底成为一个“被理想化的年代”。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找来一些追述“80年代”的访谈录、个人回忆录、纪实影像,就会得到一定的印证。那么,张楚的《姐姐》和“80年代”又有怎样的关联呢?
首先,我们需知道: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相继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文化现象,如“青春诗会”与朦胧诗的崛起、“美学热”的出现、摇滚乐的流行、人体美术的复兴、港台剧风靡大陆,等等。尤其是朦胧诗与摇滚乐的流行,它们共同的一个文化标签就是“反叛”与“叛逆”。如被称为朦胧诗派“童话诗人”的顾城的《一代人》
(1979)
基于叛逆的情感首先源于一代人对于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历史记忆,就像七月派诗人牛汉1982年创作的一首诗:
人们/老远老远/一眼就望见了我/满树的枣子/一色青青/只有我一颗通红/红得刺眼/红得伤心/一条小虫/钻进我的胸腔/一口一口/噬咬着我的心灵/我很快就要死去/在枯凋之前/一夜之间由青变红/仓促地完成了我的一生/不要赞美我……/我憎恨这悲哀的早熟/我是大树母亲绿色的胸前/凝结的一滴/受伤的血/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很红很红/但我多么羡慕绿色的青春——牛汉:《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1982)
当然,这种对于历史与传统的反思,并不一定是每一位创作者的自觉行为。因为,在这场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并不是每一个亲历并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人,都遭受了像七月诗派那样的命运。因此,在80年代的历史与文化反思中,更加强大的力量来自这个新时代的人们对于变革的共同渴望。而他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对整个过去的反思。于是,这次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就表现一股强劲的反思意识与“弑父”冲动。再如舒婷的《一代人的呼声》:
我绝不申诉/我个人的不幸/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无数失眠之夜/留下来痛苦的记忆/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心中只剩下/一片触目的废墟……/但是,我站起来了/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舒婷:《一代人的呼声》(1980)
这首完成于1980年的诗歌,后来发表于《诗刊》1998年第11期。在当期《诗刊》发表这首诗作的页面上,有一张正在耕种的黑土地的插图。在这幅插图之上,赫然出现“早春与中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0年纪念”的题头。
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到大陆摇滚乐的诞生。如台湾摇滚乐评论家张铁志所言:“过去在大陆,音乐或者文化背负着由上而下的巨大政治使命,是为国家服务。然而到了80年代后期……摇滚乐成为民间的巨大声音,并且是80年代启蒙的文化力量之一。”事实上,西方的摇滚乐,也包括大陆的摇滚乐,从诞生之初就带着叛逆的躁动,挑动年轻人的欲望,对传统、主流社会秩序即“父亲”及“家”产生反抗意识。
就张楚的《姐姐》来说,它反复在表达一种诉求:“带我回家、我想回家。”然而,对于“家”的咏叹与赞颂,在中国传统诗词及曲调音乐中,并不稀奇。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音乐、民谣-摇滚、朦胧诗等,表达的是一种对“父辈”与“家”的叛离及出走,尤其是歌者的漂泊与“在路上”状态。因此,张楚的这首代表作,不是对“家”的回归,而是对一种个体的孤寂、漂泊与乌托邦式的追寻。在对这个虚设的“精神家园”的追寻中,他同时又在呼唤一个可以“带他回家”的人,这个人,他称为“姐姐”。
“姐姐”是谁?是一个实指的对象?与这个流浪者具有血缘关系的“姐姐”?一个具体的被称为“姐姐”的且长于流浪者本人的“女孩/女人”,或者仅是对一个虚设的女性对象的概称?实际上,就歌曲本身而言,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追究这个被呼唤者——“姐姐”——与歌手张楚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甚至关于这方面的考察没有任何必要,因为我们是被这首歌曲的旋律及其所渲染的特定情绪感染。正如王翔所言:“他所谓的’回家’,是要回到一个什么样的家?为什么他要和‘姐姐’一起回去?为什么他要‘姐姐’牵着他的手?这一连串的问题,其实正内在于副歌这一连串的呐喊。这呐喊的和弦是G—Em—C—D,再循环;D和弦给人一种开放的感觉,好像这呐喊在继续延伸。回到主和弦G,这样的呐喊才有了一个终点。在这样循环不断的呐喊中,仿佛可以看到,一个漂泊的少年,和一个受伤的姐姐,在渴望着某种温暖、安稳的东西。而这就是歌里唱到的‘家’。这不是一个有着具体内容的家,而是一种内心的呼唤,一种抽象的、精神的家。”
因此,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都要返回那个特定年代的历史记忆。据当时的亲历者回忆: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某个上午,张楚穿着破烂的衬衫,坐在
(北)
师大的讲台上,第一次唱了他那首著名的《姐姐》。当时张楚对教室里的人说:“这首歌,是我刚写好的,送给我的姐姐们。”与此同时,《姐姐》还明确地表达了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对于“父亲”的抱怨:“我的爹他总在喝酒……”但是,对于这个流浪的孩子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因为“他坐在楼梯上也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
《出走》一曲中的“老地方”“老路”“老头子”所暗示的,是从那个“家”的“出走”或者叛离,这无疑成为“子一代”寻找人生出路的必然选择。返回摇滚乐的西方语境,我们在1957年杰克·凯鲁亚克的名作《在路上》、1965年纽波特民谣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的《像一块滚石》中,同样能够找到这种“子一代”对“父一代”的叛逆与出走。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的《代沟》一书中,作者在分析美国社会“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的文化差异时,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解读了“代沟”的时代与文化内涵。尤其是在从以“父辈”为楷模的“后象征文化”向以“子辈”为主体的“互象征文化”的过渡中,这种对“父辈的旗帜”的挑战,不仅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而且将更加激烈。如其所言,“在每一个后象征社会中,每一代男孩中都会出现对男性权威的恋母性的挑战,如果一个社会要存在下去,就必须应付这种挑战……后象征社会中的代与代之间的关系,不一定那么平静。在某些社会中,每一代都有造反的可能——蔑视老人所表达的愿望,从上面一代人手中夺权”。
因此,这种“出走”的冲动与离家而去的“弑父”情结,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故而有学者曾说:“中国需要摇滚乐的原因,既不是丰富艺术、解放思维,也不是促进商业,而是——启蒙。”这也就是为什么“80年代”与“摇滚情结”之间,有着扯不断的联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首《姐姐》绝对不是歌手张楚借助歌曲的方式抱怨自己的父亲,宣泄儿子对于父亲的个人情绪,而是那个时代“子一代”对“父一代”的集体性“弑父”情结。
当代知名作家柯云路先生在2005年出版了一部名为《父亲嫌疑人》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以年轻小伙子阿男的身份和口吻表达了一种压抑已久的“弑父”情结。此书的内容简介中写道:“作者‘潜入’一个年轻诗人的灵魂,用他的眼睛观察和叙述,从心理层面入微刻画了一个男孩在其成长过程中与众多父辈既卑微又高傲、既渴望承认又处处叛逆并想取而代之的复杂感受。那些他喜欢的女孩,一方面羡慕他的才华受其青春气息的吸引,另一方面还在父权的笼罩下……”
之后,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柯云路先生为我们讲述了这部小说的写作初衷。关于这段文字抄录如下:
几年前看电视节目,引发了我的一次写作。节目中几位学者和年轻人围绕着一个共同的话题讨论,现场气氛时而激烈时而沉闷,也多有让主持人尴尬的对立。年轻人普遍对学者表现叛逆,学者们也在宽和的表象下难掩对年轻人的轻蔑。两代人或唇枪舌剑或明争暗斗,让我想到了弗洛伊德的“俄狄普斯情结”。俄狄普斯情结也就是弑父情结,在家庭中表现为儿子与父亲的对抗,在社会中表现为年轻人对年长一代的叛逆。这自古以来是社会很多冲突的原动力之一,也演绎了许多惨烈或悲壮的文学故事。这种叛逆不一定都是可歌可泣的,有的甚至十分残酷。我在此前曾写过一部小说《青春狂》,讲的是一群十几岁的男女学生在“文革”中用石头将他们视若父亲般的男性老师以“流氓罪”砸死。弑父的情结以集体的“革命”行动表现出来。在此之后二十年,这些年轻人逐渐成熟长大,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当年的过失,却共同加入了悼念“父亲”的行列。现在,有关对弑父情结的联想,激发了我写另一种年轻人叛逆的故事。在各个领域,年轻人都在用他们的新声音、新手法“屠杀”年老的一代。这种“屠杀”温和了表现为革新,激烈了表现为取而代之。在时间的年轮上,欣欣向荣的进步与衰朽死去的残酷交相辉映……
在这段文字中,柯云路先生说出了20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社会转型时期进一步激化的代际之争,年轻人从各个方面发起了对老一辈人的“弑父性”的文化反叛。事实上,不仅仅是作者柯云路如此认为,大陆作家王蒙、香港作家梁文道等都曾就年轻人的“弑父”情结发表相应的言论。
而一大批文学批评家也从“弑父情结”的视角切入对鲁迅、曹禺、莫言、苏童、张艺谋等20世纪文学家或文化现象的分析与解读,尤其是80年代的诸多文化事象。例如,在王朔、姜文等人的言词语汇中,我们也不难捕捉其中所表露的一种“弑父”情绪,如《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的“野孩子”形象及其对一个年龄上长于自己且颇具几分成熟女性魅力的“姐姐”米兰的迷恋,等等。
就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来说: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到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蓝图之间,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与文化转型进一步拉开了两个时代的距离,也拉开了两代人的距离。文化滋养与家庭教育的转变在政治因素的强力介入下,一个原本基于生理差异与年龄差异的“代际关系”被彻底放大,而且它的背后交织着诸多社会文化因素。
正如朦胧诗人顾城的父亲顾工在《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一文中所言:“我越来越读不懂我孩子顾城的诗,我越来越气忿……这样的诗,我没有读过,从来没有读过。在我当年行军、打仗的时候,唱出的诗句,都是明朗而高亢,像上了膛的炮弹,像灼烫的弹壳。哪有这样!哪有这样?!我开始为我的孩子,为我们的年轻一代,不寒而栗。”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
(文化)
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弑父”现象,如朦胧诗的崛起、摇滚乐的出现、第五代导演作品中的“父亲”形象,也包括80年代的文学创作者陈染、莫言、苏童、余华等小说家,甚至包括香港新浪潮电影中的青春片。当时不仅涉及诗、绘画、小说、电影等艺术领域,也涉及流行音乐、发型、服饰等生活领域,整个社会呈现文化启蒙与雀跃的人性解放味儿,而整个文化艺术界的变革态势及其形式技法更是表现一股强劲的“弑父”冲动。
当然,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父亲”,不仅具有血亲伦理层面的含义,更是一个特定的“文化身份”,他“代表家庭和社会制度的维护者,他人命运的决定者,权力的掌握者以及精神上的领导者”。正如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对“弑父”现象的分析:“根据弗洛伊德的解释,最早的人类集体是由一个人对所有其他人的强行统治而建立并维持的。成功地统治着其他人的人就是父亲,他占有他所渴望的女人并与其生儿育女。这位父亲独占女人
(最高的快乐)
并使部落的其他成员都俯首帖耳……因此,父亲对满足本能需要的约束,对快乐的遏制,就不只是统治的结果,而且也是统治继续履行其功能的心理前提……一体化了的家长、父亲和暴君把性欲和秩序、快乐和现实统一了起来;他唤起了爱和恨;他奠定了人类历史的生物基础和社会基础。要是消灭了他,也就消灭了长期的集体生活本身,也就恢复了快乐原则的前历史的和潜历史的破坏力量。”
于是,一种被社会变革激活的年轻一代的“弑父”心理逐渐浮出水面,并成为那个时代最突出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张楚的《姐姐》里一方面表达了对于“父亲”的怨恨,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那个原本的“家”的叛离,“离家出走”成为弑父者必然的选择。
记忆:青春的激情
无论是处于流浪、漂泊中的张楚,还是那一批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乐手,他们正值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与“弑父”情结中,本身就激荡着一股强烈的青春激情,“那时唱的歌也都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青春啊青春’,整个社会洋溢着一股朝气蓬勃的感觉”。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岁月,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青春主题。但是,80年代的社会转型纠结着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等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又进一步激活了那个时代的代际关系及青年一代的自我认同。具体来说,那个年代的代际关系具有复杂的社会因素,从而使弑父、青春、欲望三股力量交织在一起。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青春的激情”。其实,无论是对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摇滚乐,还是对80年代的张楚等摇滚乐人来说,音乐、青年文化与社会反抗的有机结合,是摇滚乐一直不息的思想根源。20世纪80年代彻底宣告了父辈们在战火中绽放青春的革命人生的结束,本打算参军服役奉献青春的年轻人遇到了那个年代的大裁军。随着当时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和中国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方针的调整,中国军队从80年代中期的临战备战状态,真正转入和平建设轨道,并积极主动地寻求一种和平化的国际环境,着力提升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实力。在这样的历史巨变中,无以安放理想的青年一代必然寻找另一种可以表达自我、实现自我的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是:许多革命歌曲、爱国歌曲、歌唱乡土情怀的歌曲被这一代年轻人注入一种青春化的活力,它去掉了传统唱法的高、硬、快、响,也去掉了抒情表意,而是在注入个人化的情感基础上,注重指向歌唱者本人内心的骚动和乐观心态,并洋溢着一股青春的气息。其次,我们要说的是“欲望”:这个词曾一度被中国社会和民众视为一个具有否定意义的贬义词,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社会主义新中国强调每一个个体的“阶级性”“人民性”,而不是基于身体的各种欲望。但是,1979年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方针首先认同了每一个人的欲望的合理性。
就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领域而言,首先是对“主体性”的强调与个人价值的重新体认,一种尊重个体、保护个性的人道主义的人学观念受到学术界同人的追捧。于是,重回世俗生活与关心人的基本需要,成为一种颇具历史意义的启蒙性话语。当时的文艺界积极拥护思想领域的新变革,人性的大讨论与启蒙话语,成为当时文艺界的主格调。朱光潜将“人性论”视为《手稿》的核心价值,李泽厚借康德哲学的理论资源畅谈“主体性”问题,刘再复则以西方文学的历史实践推崇文学中人的价值,故而,“一个总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如此等等。例如,在1957年3月因《论“文学是人学”》而受到批判的钱谷融先生,在1980年由冯牧主持的《文艺报》召开的会议上,以《〈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为题做了发言,并将此文发表在1980年的《文艺研究》上。该文如其所说:“虽然说是自我批判,但基本观点没有任何改变,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之后,呼唤人性,挖掘人性,美化人性,成为当时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于是,汪曾祺的《受戒》
(1980)
、戴厚英的《人啊,人》(1980)
、张贤亮的《绿化树》(1984)
等文学作品大受欢迎。
追叙历史,我们会发现:20世纪的中国社会,自人民政权建立以来,尤其是自19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与其说是与一切破坏人民专政的资产阶级及其腐化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不如说是与人性的内在的世俗化欲望作斗争。
或者一种似乎更为妥帖的说法是:在社会政治斗争与阶级矛盾问题上,我们的党和人民与一切试图破坏人民政权的资产阶级及其反革命分子进行着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而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斗争却更为隐蔽、幽暗、尖锐,它要在短短的时期内经受多重文化、阶级、利益和欲望的殊死斗争,一方面既要清除我们每一个革命者、党员、普通老百姓内心深处传统的封建思想余孽,另一方面又要狠狠地扼住我们每一位革命者、党员、普通老百姓肉身欲望的自由流溢。80年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同志作为总设计师具有惊人的魄力,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着实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绿灯!
而我们在前面提到8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文化现象:朦胧诗、摇滚乐、迪斯科、人体美术、港台剧,等等,其贯穿一致的就是放开了对人的合理化欲望的政治化管制。又或者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思想文化领域里,文学对于“人性”的关注,流行音乐对于个人情感的抒发,人体艺术对于身体美感的直观呈现,港台剧对于世俗情欲的镜像化演绎,等等,就像当年喇叭裤、健美裤的流行一样,将身体的欲望化曲线借助各类文化事象合理地体现出来。它们以文学的、艺术的、音乐的、影视剧的、服饰的等众多名义,不断地开拓人们对人性、对自我的观念启蒙,宣扬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与乐观的文化心态,而它背后的游戏动力却是一套严肃的欲望政治学。即在思想文化的带领下,不断地解放人们头脑中残留的那些传统农耕文明时期的消费理念,一种固守着传统廉耻观与积攒型生活的生计方式,并激励人们大胆地追求一种新的生活。这或许就是蕴藏于中国民众内心深处的改革的潜在动力。至此,来自民众的呼声与知识分子的诉求,正好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然,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这种久抑的青春欲望还具有一定的理想化成分,甚至具有一种宏大叙事的书写模式,如1980年老版《庐山恋》中的爱情叙述与渴望祖国统一的爱国主题。然而,当这种“青春的激情”与“合理化的欲望”注入对过去历史的反思与传统文化的检讨中时,一种更加崇高的文化情绪应运而生。这在历史巨变的转型时期,既为欲望的合理化赋予了时代的伟大意义,又为“青春的激情”赋予了一种理想化的书写方式。
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回过头再来看这部电影,耿桦与周筠的爱国热情自然是打动了当时的观众,但整部影片中青春的欢愉、爱情的甜蜜和那激荡人心的“吻戏”也让中国民众久抑的欲望得以释放。正如某影评所言:“庐山恋,让中国电影走上了世界,也突破了传统,在刚刚开放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人对‘吻戏’有着极少的接触,庐山恋,让封闭中的中国观众,见识了一种新事物,这就是——我们可以自由的生活。”至此,在那个交织着多重复杂因素的年代,弑父、青春、欲望三股力量交织在一起,书写了那个时代特定的“青春记忆”。
个性:解放与欲望萌发
当然,《姐姐》这首摇滚乐最大的特色是它以个性化的方式,表达了一代人集体的困惑、迷茫与追求,并交织着这一代人的青春、爱情、欲望和理想。在这一方面,它既融入了歌手张楚的私人化体验和个性化的情绪,又从私人化体验逐步上升到一个共同的爱情主题,并最终实现一种集体性的弑父行为。尤其是这里面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姐姐”形象的出现,使它既不同于一般的爱情歌曲,又迥异于流浪者纯粹的弑父情绪。
无独有偶,顾城在1987年写了《铁铃——献给在秋天离家的姐姐》一诗,“最纯粹的诗人”海子在1988年写下了《日记》,这首诗是一个漂泊、孤独的个体对“姐姐”的倾诉:“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而在1989年,张楚唱出了摇滚乐中的一首经典曲子《姐姐》。之后,我们在张贤亮的《绿化树》
(1984)
中找到了“马缨花”,在王朔的《动物凶猛》(1991)
中找到了“米兰”等类似于“姐姐”的角色。
我们在前面曾说过:我们没有必要追究这个被流浪者寄予“带我回家”之望的“姐姐”在歌手张楚私人生活中是不是存在一个实指的对象,而应该把“姐姐”看成对一个虚设的女性对象的概称。首先,我们先从两性青春心理学来说,可以发现每一位正在经历青春期的男孩,几乎都会将自己身边的某一个成熟的女孩/女人假想成自己的“初恋情人”或“心中的女神”,就像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对于米兰的迷恋。或许因为女孩较男孩早熟一些,尤其是比男孩年长几岁的女孩身上所散发出的一种成熟的异性气息,不断地诱发着男孩生理和心理的成长。于是,“姐姐”,即那些具有成熟的异性气息的女孩/女人,就会成为男孩青春期懵懵懂懂的爱情对象,或者是一种“影子爱情”。
因此,在这首歌曲里,委婉地表达着一份歌者的爱情诉求,尽管并不一定是主导性的情绪。而从歌词“你该表扬我说今天还很听话/我的衣服有些大了/你说我看起来挺嘎/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挺傻……”可以看出:无论是年龄还是心理,“我”都比“姐姐”稚嫩,故“我”也很尊重、听从、认可这位“姐姐”,尤其看重这位“姐姐”对于自己的感情。我们从歌词“姐姐/我看见你眼里的泪水/你想忘掉那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他们告诉我女人很温柔很爱流泪/说这很美……”可以进一步看出:这位“姐姐”已经经历了爱情的情感体验或具有爱情阅历,而且在“我”的眼里,“姐姐”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而不是一个懵懂、幼稚的女孩。一方面,正是因为“姐姐”具有成熟女人的味道,它能唤起的是“我”对异性的懵懂的爱;另一方面,因为“姐姐”身上有成熟的母性气息,它能抚慰着离家出走的孤独的“流浪者”,尽管这可能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流浪”或“离家出走”。
其次,就20世纪80年代摇滚乐的符号表意与性别叙事而言,在男性意识的主导下,借助“我对你唱”的抒情模式,摇滚乐中的情感召唤对象更多倾向于那个不明确的“她”,甚至在一些女性摇滚乐手的歌词中也是如此。因此,“摇滚歌中的抒情对象——女性,都是一个虚指,作为文化性别范畴的’你’
(或‘她’)
,并没有固定的、具体的形象,却常常是男性(抒情主体)
欲望及幻想主体的投射”。
最后,这位“离家出走”的流浪者对于“姐姐”的反复呼唤,或许并不仅有自我的爱情诉求,还有一种寻找归宿或“带我回家”的殷切需要。而这个“家”既不是那个由父权操控的“原来的家”,也不是一个具体的实指的居所或安身之处,它是一个可以安慰流浪者孤独的心灵和安放青春的地方。流浪者反复呼唤“姐姐”“带我回家”,因为他已经“有些困了”,并要忍受穿越陌生的人群的“孤单”,这一切都在传达着歌者的孤独、困惑和迷茫。正如李一所言:“‘姐姐’某种意义上正是’我’内心对世界的一个正面投影和成像,她是作家塑造和虚构出来用以对抗和反思他对于世界的否定、批判以及绝望。”
而就那个年代来说,对于那一代青年人而言,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他们,既会遇到每一个年轻人都会遇到的青春的迷茫、理想的迷茫,又会陷入由时代造成的历史转型期的困惑,这些多重的困惑交织在一起,必然深化了那个年代青年人人生选择的意义,也造成了他们心理上的分裂与情感的迷茫。正是在这种多重迷茫之中,他们等待被“姐姐”拯救或被“爱情”拯救,这也就为“姐姐”和“爱情”赋予了多重意义,因而并不停留于字面上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它也强化了80年代青春叙事的个性化与时代性。
1981年,李泽厚先生首先站出来在《画廊谈美》中为年轻人辩护:“在那些变形、扭曲或’看不懂’的造形中,不也正好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破碎心灵的对应物吗?政治上的愤怒,情感上的悲伤,思想上的怀疑;对往事的感叹与回想,对未来的苦闷与彷徨,对前途的期待和没有把握;缺乏信心仍然憧憬,尽管渺茫却在希望,对青春年华的悼念痛惜,对人生真理的探索追求,在蹒跚中的前进与徘徊……所有这种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混乱的思想情感,不都是一定程度地在这里以及在近年来的某些小说、散文、诗歌中表现出来了吗?它们美吗?它们传达了经历了无数苦难的青年一代的心声。”
尽管李泽厚先生当初心里想着朦胧诗,但他的这番话却最符合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境遇。尤其是那句“政治上的愤怒,情感上的悲伤,思想上的怀疑;对往事的感叹与回想,对未来的苦闷与彷徨,对前途的期待和没有把握;缺乏信心仍然憧憬,尽管渺茫却在希望,对青春年华的悼念痛惜,对人生真理的探索追求,在蹒跚中的前进与徘徊……”它既符合朦胧诗的内在情绪,又是20世纪80年代摇滚乐的情绪主调。
当然,相比朦胧诗的诗性写意来说,摇滚乐所彰显的青春激情更直接一些;相比朦胧诗的审美形式来说,摇滚乐与反叛性情绪更贴近一些;相比朦胧诗的精神性诉求来说,摇滚乐与身体的欲望更亲近一些。之后,一切关于这种青春的激情、反叛性的冲动、身体化的欲望都在逐渐商业化的大众文化中找到了合理的宣泄途径,而此后的“摇滚乐情结”也必将渐行渐远。
故此,学者王一在《音乐在世纪末的中国:后现代主义与当代音乐》一书中,对中国乐坛及民众的“摇滚乐情结”做出了这样的描述:“80年代后期的中国摇滚乐是一个神话。这并不是由……歌唱本身决定的,而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心态尚能容纳神话。进入‘新时期’以后知识青年曾经有过的诗意的激情尚未逝去,而摇滚乐所表现的‘个性解放’恰与当时‘文化热’所追寻的神话式理想合拍,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反而抬高了摇滚乐的身价,于是,摇滚乐已不仅是它本身,它承载着美妙自由的现代伊甸园的神话。进入90年代之后的中国已经无法容纳神话,在走向商品化和大众传媒化的过程中,摇滚乐的‘精神’也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景。”
观念放开了,身体解放了,欲望的市场也就形成了。正如人称“迪斯科女皇”的张蔷在接受一次采访时所说:
“两年前陪林强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节目,听他把格物致知的’格物’,强行或者说故意解读为‘克制物质的欲望’。那么请允许我也对‘启蒙’做一番望文生义的解构,将之强行解释为‘开启荷尔蒙’,……荷尔蒙意味着性启蒙,也意味着消费文化的开启,而迪斯科比摇滚乐稍稍早了一点,引爆了一代中国青少年的荷尔蒙。”
无独有偶,当1994年张楚出版第一张个人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时,魔岩唱片老板张培仁在文案中明确地写道:“这是1994年的春天,空气中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与此同时,张楚在“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里唱出了这个时代的“欲望抒情”,也以此宣告了针对体制的抵抗与反叛精神滑入经济大潮的“潮流之中”。可以说,张培仁准确地把握住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征候的一个关键词:“欲望”。
与此同时,正如80年代中国民众的记忆碎片中所呈现的:喇叭裤、蛤蟆镜、摇滚乐、录音机、红棉吉他、地下舞会、高跟鞋、纯真情书,等等,这一切都体现在“青春一代”的身上,既是“他们”的欲望,又是那个时代中国民众压抑已久的欲望。学者马军驰在《为什么追忆1980年代?》一文中就说道:“在体制变革的层面,它释放了国家的生产力和民间的能量,使中国人在这个10年中第一次开始有了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可以选择、可以追求的日常生活。即便全社会都醉心于诗歌、哲学等宏大叙事,牛仔裤、交谊舞会、美食一条街、灯光夜市、黑白电视机和万元户这些1980年代的新生事物仍如急管繁弦紧扣人们的心扉。”
而在这之前的1979年,香港歌手张明敏回忆最初来内地时的印象:“比如说当时内地人都穿中山装,女的也穿得很暗淡,给人感觉很压抑,和香港的花花绿绿很不一样。当时内地没有冰块,啤酒也是热的。”然而,短短几年的时间,“街上去看,什么样儿的都有:超短的、加长的, 紧身的、宽松的,镂花的、滚边的,古典的、前卫的,露肩露背露肚皮的、半遮半掩半透明的……真是百花齐放,美不胜收”。
因此,广州美术学院李公明教授认为80年代的文化启蒙有两只手:“一只手通向理论美感的区域,像关于美的问题、人性问题;另一只手拉扯的是生活的现实现象,包括服装、流行歌曲、发型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文化评论人张晓舟认为:“迪斯科只是通往八十年代的钥匙之一,而朦胧诗是另一把钥匙,这首歌
(《我的八十年代》)
借迪斯科也歌唱了文学,荷尔蒙和思想启蒙俨然得以统一。”
印记:理想中的中转站
从朦胧诗到摇滚乐,再到流行音乐一统天下,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的历史转型时期,“文化热”的兴起不仅仅是对总体现代化的积极响应,也不只是思想文化领域催生的璀璨之花,更重要的是它以“非政治”或“反政治”的姿态连接了一种政治话语向另一种政治话语过渡的特殊使命,而这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政治使命”。
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面对经济体制的大改革与政治决策的调整,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主张与变革诉求最终曲折地为文学艺术的繁荣注入了一股躁动的力量。左右腾挪、跌跌撞撞的主体性诉求与启蒙使命,终于为文学艺术乃至文化活动赋予了一种特定的历史使命。当然,这一切似乎只是思想文化领域的特定事象,但它又不仅仅是只满足于文化层面的解释。之后,当这种语境消失之后,诗歌、小说、音乐、电影等也就逐渐退回一种正常状态下与生活的互动性亲近的关系中。
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世俗化的欲求与大众化的力量,在市场经济体制与消费文化中开始寻找释放激情与希望的宣泄口。因此,作为过渡期的“80年代”,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既定的事实,它有存在的充分理由和依据。然而,它与一大批文学批评者,包括各色人文学者,以及诸多处于复杂动机下的社会诉求,又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密切关联。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骚动与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相互勾连,但又抵牾、冲突、纠结不断。它们之间复杂而矛盾的内在张力,体现了那个年代特定的政治气候。在拨乱反正的局势下,各个领域都在跌跌撞撞地进行着改革的实验与探索,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中所出现的一系列现象更是彰显了知识分子对改革的诉求。
现如今,当我们略去那些磕磕碰碰、弯弯绕绕的细枝末节后,回首80年代之于今天生活的启示意义,终会发现:80年代,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渡期”,它承接了70年代末期的“革命-改革”,又为90年代的市场经济完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铺垫。因此,“80年代”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是一个理想化的“春天”,而是一个必要的“中转站”。
整合丨吴鑫
编辑丨西西
校对丨翟永军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八十年代并不是理想化的“春天” 而是必要的“中转站””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