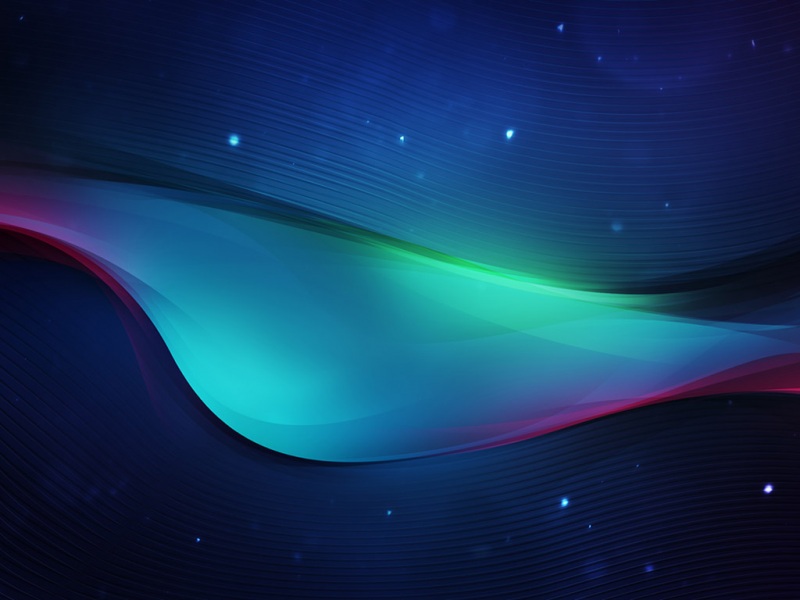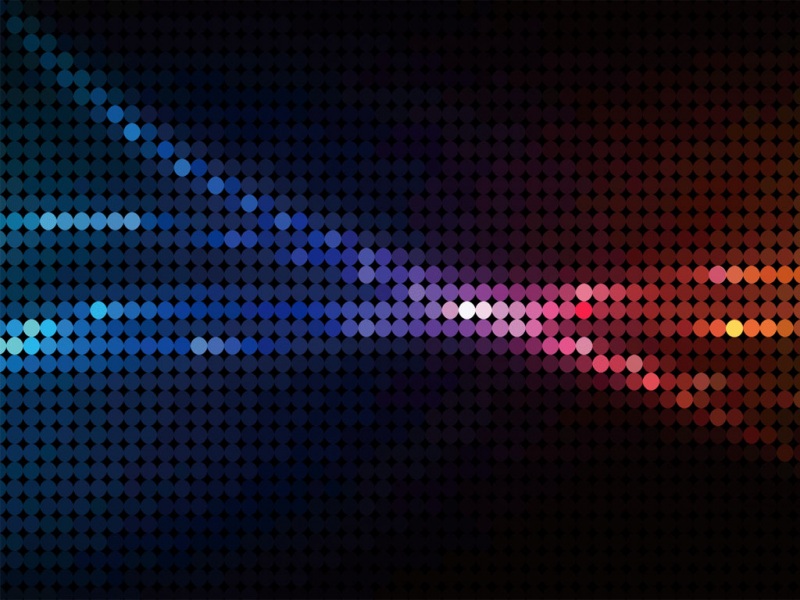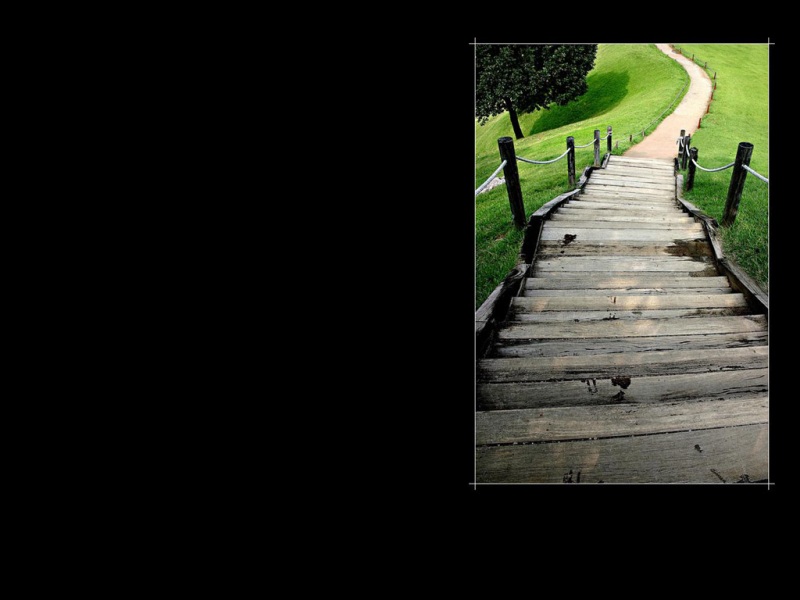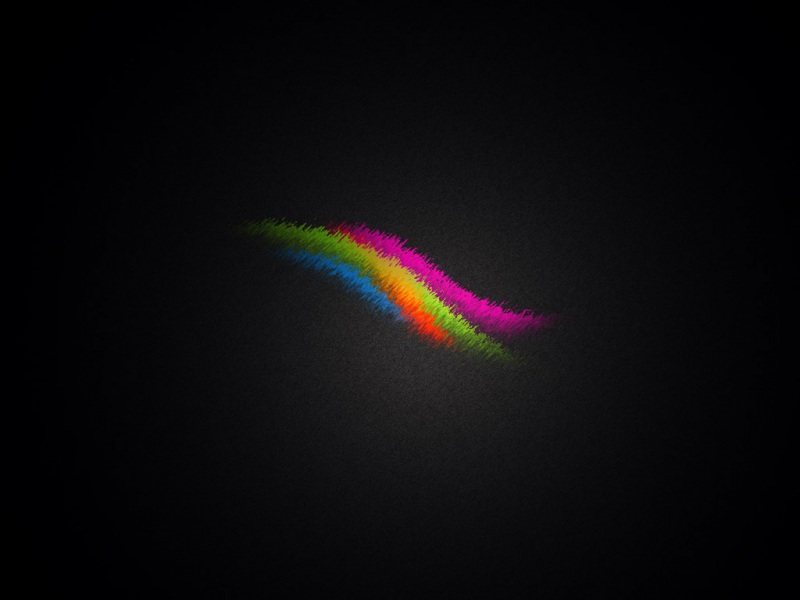提示:本文共有 16461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33 分钟。
第二十五回 乾隆初治 《石头记》问世探路
话说曹与母亲正在议论往后曹家的兴衰荣辱之道,忽听家人来报,说是坊间传得沸沸扬扬:雍正皇帝驾崩,弘历继位。从明年起改用‘乾隆’年号……
母子二人先是一惊,只怕宫廷里再起内讧;好容易苦苦挨过了十二三年,略有些好苗头,又换了个‘乾隆’皇帝;不知又有什么新主意?再听说是弘历继位,心里又有些许宽慰,但还是不甚踏实。李氏毕竟做过女官,后宫之事,见多识广,不无忧虑,道:“按说胤禛今年只有五十七岁,此前也无龙体欠佳之说,那‘追封曹家曾祖’的旨意,还是几天前的事儿。那内府来人还说过,皇上经常通宵达旦批复奏折,要不便与弘历彻夜密谈。难道累死了不成?后宫之事历来是本‘糊涂帐’,也难说是别有用心的人谋害,十三年来,树敌太多。手足之间,斗的跟乌眼鸡似的,难保没人暗地里下毒手。不过,宝亲王弘历虽然已有二十四岁了,继承父亲皇位也是顺理成章的,决不会,冒天下之大不违,杀父轼君,自讨骂名?若说‘因果报应’,老身早已不信的了!再不就是圣祖康熙皇上留下‘锦囊妙计’?再不……”
曹道:“管它如何呢!依我看秋谷叔的‘韬光养晦’才是‘锦囊妙计’!静观以待就是了。等天佑回家时,便——”
李氏道:“说得也是,可霑儿有些日子没有回家了。难道连新媳妇也忘了?”
正提起天佑时,只见曹沾风风火火闯进门来。本是先来问候奶奶,但见叔叔也在,便脱口而出:“宫里出了大事儿了——” 李氏道:“别急!慢慢说,把你媳妇也接来听听。”
原来天佑眼下在内务府属下衙门做‘笔帖式’(满语),刚刚升迁至八品。平时无非做些档案整理、奏章的满文、汉文翻译,抄写文书之类的事儿,曹沾不久前还是末级九品,近来升迁八品,这‘笔帖式’虽是九品小吏,却也是朝廷命官;且是八旗升官最快的一条‘官道’。曹天佑沾(‘霑’,‘沾’的异体字。)了正白旗藉的光,也沾了祖宗名望的好处,若有当年曹家与爱新觉罗的关系后盾,曹天佑尽可坐等飞黄腾达的。然而今非昔比,因此曹沾百倍勤奋,也是赶上时候,正是雍正皇帝‘先打而后拉’的治国之道已经走上‘拉’的一步。最近几天只因誊写过机密,上司一概不准回家。只等到驿马将《告示》传递到江南,这才跑回家来。(哪里又有空闲创作《红楼梦》?)
只听曹沾断断续续说道:“……按律,有些事儿不可外传,如今时限已过,就说也不妨。雍正皇帝是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在圆明园驾崩的。前一天还有人誊写过雍正皇上的批折,怎的就突然……私下里有人怀疑被害,却不敢说出去。第二天便有弘历写的手令,将宫里的几个炼丹烧汞的道士抓了起来。于是有人猜测必是喝了妖道的毒药……内府的人也不相信:皇上倒是迷信仙丹神药不假,可又疑神疑鬼,每每用药之前,必由太监尝过。或许皇上几天劳累身子弱,经不起猛药,也不得而知。……只是,有件事儿与咱曹家有关,据说雍正皇帝批示——”说到这里曹沾卖起关子来,故意道:“反正是好事儿,弘历一律照办。过几天就清楚了……”
果然,几天之后,刚刚登上皇位的乾隆皇帝,仍用‘雍正’年号,于雍正十三年九月二日正式诏示:追封曹振彦为资政中议大夫,原配欧阳氏、继配袁氏为诰命夫人。诰封曹玺为光禄大夫。
又过了半月光景,内府传达旨意:说是‘各项宽免欠款内,叠涉曹家旧案,皆在宽免之数。’曹家上下无不欢欣鼓舞;唯独曹总是有些心思,常常独自坐在那半间书屋‘梦坡斋’里,不知写些什么、想些什么?父亲的《遗稿》,也是久久不动的了……
却说曹此时已是年过了四十奔五十的人了,难免在百无聊赖之时,多把往事回忆。自己虽然生在温柔富贵之乡,自幼便带了一身病残,奶奶临终前答应自己出家做和尚,而爹爹不允;爹爹临终前答应了,母亲又不允,说是留下帮助颙哥料理江宁织造业务。谁知只经营了三年,颙哥便走了。江宁曹家若能从此离开织造府,应是上上之策;只因一念之差,竟惹出诸多事端,连累曹家不说,自己白白地受此苦难已是十年有畸。曹越想越糊涂,竟骂那康熙老儿多管闲事,节外生枝……可恼,可恨……。
此话刚刚出口,但见门外雪地里走过一个人影儿,只怕是隔墙有耳,祸从口出,闯下是非来!那人只管朝‘梦跛斋’走来,停在窗外。只听得窗外长叹道:‘别埋怨康熙皇上了,他也是好意。曹家不做忘恩负义的事儿。都怨我,当初没听你奶奶的话……你从此以后,好之为之。……皇家的事情,你会慢慢明白的……我和奶奶会保佑……切记‘急流津’之觉迷渡口……’说罢,那人一跛一拐地朝院门外走去。曹这才记起那人正是朝思暮想的爹爹‘跛足道人’,赶紧起身追去,只一动弹,便醒了过来,原来是南柯一梦,自觉得房内寒气袭人,打了一个冷颤,案上的半支腊烛似明似暗,昏惨惨如青灯将尽……
自从在半间书屋受凉以后,曹一病不起。一连几天高烧不退、胡言乱语,昏迷不醒,急得全家团团转。只因曹尚是犯官之身,哪得太医院诊治,曹沾只得私下求医,也不见好转,无可奈何就将送终得寿衣也就准备下来。李氏心痛不已,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拦他入那佛门?至少如今还守着他奶奶、爹爹的身旁。就这样不死不活,时醒时迷地挨了两个多月,已进了乾隆元年。
不久,曹总算活了过来。只是身子太弱,起不得床的。每每由老仆照料。加上这时曹沾之母马氏已经病入膏肓,全由紫烟一人照看,已是难为的了。可怜一个赫赫扬扬已近百年,两代诰封中议大夫、光禄大夫之家,子孙后代落得个凄凄惨掺。那刚追封的两代诰命,只可留给后人增修《曹氏宗谱》,做炫耀点缀之用!
菜市口曹家的近况,不知是否传到了乾隆皇上的龙耳。不久,内府差人前来十七间半房,传曹、曹天佑前往内务府听旨。哪知曹骨瘦如柴,卧床不起,如死人一般;然而大病之后,神志格外清醒。家里人还曾疑惑:莫非昏迷半月,灵魂出窍求仙访道去了?曹便命曹霑到梦坡斋取来一封信函,交于公差代呈内府,曹霑随同进府听旨。原来乾隆皇帝下了一道诏谕:封曹朝议大夫,职内务府郎中;曹寅之孙曹天佑,迁六品州同职。
曹霑代叔叔叩谢龙恩后,便从差人手中取来那信函,交于上司。原来曹在大病之前的那天夜里,正是在修此书函备用,信中说得恳切,把自己的前前后后说得十分详尽:尤以体弱多病、身有残疾,其貌不扬为由,请辞。内府另附一折,奏请皇上,言明曹家状况。乾隆皇上最是体恤老臣,也体味到曹家实有‘激流勇退’之意;就做了个顺水人情,便在折子上批下,‘知道了’三字,又命内府定期给予曹家些抚恤银两。不再赘述。
却说曹霑回到家里,把那浩荡皇恩着实述说了一番。全家无不欢欣鼓舞。唯有已卧床三载的马氏,闻知霑儿升了六品州同后,只是心里明白却已说不出半句话来,流泪不止;过了两天,泪尽而逝。可怜这金陵女子,自二十几岁便做了寡妇,苦苦守着曹颙的遗腹子霑儿,已是二十有一载,今见儿子有望,虽是不舍也还是放心的到那太虚幻境,寻找曹颙叙说去了……。霑儿、紫烟哭得死去活来。从此
霑儿便守孝在家;上有年近八十的祖母,又有卧床不起的叔叔,那六品州同的外任(丰润《五庆堂曹氏宗谱》仍以‘州同’记载),便成泡影。期间,也常去内府帮忙做些‘笔帖式’的旧业,得些奉银养家。
随着天气渐暖,曹渐渐能下得床来,只是弯腰驼背更甚。直不起身来,加上身体消瘦,活脱脱的一枚扭曲了的笏板。每天由老仆掺扶到李老夫人房内陪着母亲聊天,古往今来、天上人间无所不谈。
一日,不知怎地议论起‘立地成佛’的话头来,李氏道:“我一直纳罕,胤禛一登基,便何等凶狠,就连手足之情也是顾不得的;到后来善心忽焉!难道是宫里的那几位道士传授了什么禅道至理而大觉迷,便立地成道?”
曹道:“这也难说!大凡失迷之人,一旦觉迷,一念之差,便如换了个人似的。我倒是不信鬼神、梦幻之说的。不过,俗话说,夜里梦的,白天想的。或许是把《红楼梦》看得多了。睁眼闭眼儿都是梦,……” 于是便把那日在‘梦坡斋’梦见爹爹的黄粱美梦,当成笑话说给母亲听。李氏道:“哪里是你爹爹托梦与你,必是自己整天家把个‘知机县急流津觉迷渡口’当成心事……”
曹道:“说得也是!自己也纳闷儿,回想生病的那些日子,不分白天黑夜,一合上眼便是奇奇怪怪的世界,就连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也是见过了的……”
李氏道:“反正闲着没事儿,不妨说说,当个笑话听听也好。”
于是曹便把那夜见到雪地里一个黑影儿,远远向小书斋走来……绘声绘色地说了一遍。李氏道:“那都是你自己想说的话,一入了梦境,便招来神呀鬼呀的。”
曹笑道:“还有更荒唐可笑的哩!——” 看看母亲想听,便继续侃道:“那还是我高烧不醒之时,只觉得身子跟铅砣似的,动弹不得,忽然又变得轻飘飘的,被一阵小风吹到半空,往下一看,见床上还躺着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我还寻思:大约故事里讲的‘灵魂出窍’,今日竟被我亲眼见到;再一想,不对!……”
老夫人大笑道:“你该先摸摸自己的衣服有‘缝儿’没有,再看看自己有影子没有?若都没有,那才是鬼魂的了。……”
曹一本正经地说道:“哪里还来得及?那阵风儿早把我吹到一处比‘大观园’还大百倍的一个园子上空。但见那园子里也飘出一个中年人来。他见我来到这宫禁之地,大惊。我说寻找我爹爹——当年江宁织造曹大人。那人倒也爽快,说,他认得的;便带我寻去。果然在一座大山下,见到爹爹跟一个似曾相识的老头儿正在翻看一摞书卷,也不理我。我站在一旁,见那书卷字迹,分明是我抄写的八十回《石头记》,便喊道:这书被赵执信带到博山县(梦中竟未忘刚刚设了两年的博山县。)去了,如今还不敢面世,如何落在你们手里?爹爹这才抬头,训斥道,赶快回去!这里是你来的地方么?便拽着我往山外跑去。半路上遇见那中年人在向一位老者哭诉,断断续续听他说,……如何说我心狠手辣、残害手足?难道他们对我起善心的么?不是我死就是他活,许多旧臣被您惯坏了,目无朝纲国法,不成体统。儿臣只是‘矫枉过正’而已,……如何让我背上永世骂名?……我问爹爹,那人是谁?说老者是当年人世间的一位皇上,人称康熙的;那个人便是刚刚离开人世不久的雍正皇帝。我还后悔,何不多听点儿。爹爹说,天机不可泄露!便把我推下山涧的密云之中。睁眼一看,我还奇怪,怎的周围的人都在哭泣不止……”
老人笑道:“就知道你偷‘天机’去了,必定返回的。若不那天机一文不值。谁知你一去不回,几天之后,才带回来这点儿连小孩儿都知的‘天机’来,岂不伤心……”
母子二人又聊了一会儿,老夫人便命儿回房歇息,不予言表。
话分两头。
再说,如今离京千里之遥的博山县,赵家父子自从康熙五十九年山东大旱,离家前往苏州,一住就是两年有余,雍正二年返里时,又在扬州住下。这年秋后离开了扬州,一路上不紧不慢,直到暮冬方到颜神镇。赵执信离家四年,再见那‘秋沟’(即‘秋谷’俗称),大有【归去来兮,田园将芜】之叹;而无【乃瞻蘅宇,载欣载奔】之乐。于是吟成《归舟》一首曰:
望齐门外望青州,一室欢声入棹讴。(苏州古城望齐门)
十幅风帆半城月,最难图画是归舟。
原来秋谷在苏州、江宁、扬州期间,以及途中,遍访旧友,广交门生;秋谷又是何等聪明之人,早已把个‘国脉’诊断得十有七八。眼下人心不稳,国必不宁。于是便安心整理他那秋沟里的破屋荒田,一面抓紧赵庆的学业,以图科举。
一晃便到了雍正九年。入了六月,青州一带大雨成患。一日,赵执信独坐草堂,望着屋外大雨不停,叹息不已。忽见秋沟口处一年轻后生,头戴斗笠,怀里紧紧地搂着用簔衣裹着的一个包袱,一拐一拐地涉水而来,先在草亭下驻足整理。秋谷隔窗望去,只见这后生衣衫褴褛,也不曾认识的,便唤庆儿出门接应。那后生跟随庆儿进门,秋谷还未来得及端详,便扑通一声,说不上是跌倒还是跪倒在秋谷面前,伏在那包袱上,痛哭不已,竟也说不出半句完整话来。隐约听得似‘德州’二字的喃喃声,那后生晕了过去……
这后生姓冯,名德培,家住德州。两月前启程,步行五百里,带着爷爷的五百首诗集遗稿,前来山东,请求赵执信为序。原来德培的爷爷冯廷櫆,号大木,康熙十七年与赵执信同场乡试中举,次年赵执信殿试二甲进士,隔年冯廷櫆第进士,与秋谷同在翰林院。二人成为挚友,年轻时共作《诸葛铜鼓歌》,康熙十分赞赏,一时传为美谈!后来冯廷櫆官运不旺,三十几岁便死在任所;既殁三十有一年。从此家道中落,难以生计。其子孙多依种田、小本经营为生。近几年水、旱、蝗灾不断,庄稼不长,官府苛捐杂税却疯长。大木子孙原本攒下几两银子,想为德培雇上一头卫驴,前来博山求爷爷的好朋友为那诗稿作序;也是子孙多年的意愿。谁知德培舍不得那几两银子,竟步行五百里,两月而到。
赵执信看着德培黄瘦的面孔,细看便是大木当年模样,心里一阵悲痛,道:“你先住下,待我几天后写好了凡例,还有我写的几首和诗一并抄去。” 接着又问了大木后人如今还读书否?的培答道:“爷爷留下的门风,哪能不读?弟兄们,只是做了秀才后,如今实在念不起了,没法子……” 秋谷点点头,不语。
几天之后,赵执信撰《冯舍人遗诗序》毕。先与德培看,德培只读到开头:【德州冯大木先生,余与同举于乡,兄事之。及后同在馆阁,以诗相资也。朝士有得诸葛孔明铜鼓者,先生与余……】便跪在地上,已是泪流满面,不可卒读。执信让他起身过录一遍,德培执意跪着读完,方起身端坐,恭恭敬敬地抄写下来。秋谷见是娟秀柳体一气呵成,赞赏不已。德培道:“孙儿字迹写得不够功夫,家中弟兄多胜于我。” 秋谷又将《雨中得大木遗诗题感》怀旧诗十首交于德培过录。便与赵庆到门外草亭下,不知议论些什么。
晚饭时德培有回乡意思,道:“趁着几天无雨,打算近日起身,还是慢慢走着回去……”
秋谷道:“多住几日不妨!我还有事交待……” 于是便把半部《石头记》的 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不过只说是从南回路上购得的,此书精妙绝伦,带个抄本回去,多抄写几部,不必张扬,就在乡间庙会地摊儿上出售,若有人问起,只说祖上传下的。每抄一部,最少也能赚他十多两银子,补贴家用;还可从书中学些诗词文章、做人道理。
赵庆插话道:“这书只购得八十回,我去年抄了二十几回,试着找了个地摊儿代售,当天就售了八两银子。那笔墨纸张算起来也不过一两。后来那摊主见到我,还想要后面的几回,我说没了,他紧追不舍,于是就说还仅存四十回以后五回,那人二话没说,付我五两银子,只是成色差些……”
三人大笑。 德培站起身来,恳求道:“赵爷爷若是可怜孙儿,就把这书让孙儿来抄;俺们全家一年也难挣上十两银子……”
秋谷道:“先别急!爷爷本来就想为你谋条生路,走前爷爷送你一点本钱,回家后,就以抄书为业,或做些小本生意,补贴家用。你爷爷如若在世,也会对此书佩服不已的。我今年七十整,在翰林院时什么好书没见过?最佩服这《石头记》!【书中自有万锺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修身齐家做人的本分,书中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边抄边学,一举两得,自有好处……千万别学本县蒲家庄蒲松龄老爹笔下的《书痴》便是了!可惜蒲老已故一十六载,要不还不知有多少妙文 呢……” 又转身对庆儿道:“你不妨送德培一趟,先到济南府看看你姐夫姐姐,然后到东昌府,拜访当年翰林院的老友及我的门生。不要久留,走运河北去德州,一切安排妥帖方可回来,……” 德培感激涕零,难于言表。
几天之后,赵庆、德培带上《大木遗诗》及《石头记》过录本上路。临行前秋谷将曹当年在扬州托付的一千两银子,只先取出八十两交与庆儿,自己拿出二十两交给德培,说是路途用。
送走庆儿德培后,秋谷望天长啸:“天助我也!” 心想:鸿文既能泣鬼神,岂无苍天护佑耶?……
果不出所料。仲秋节前赵庆回到颜神镇。说冯家子孙见到书稿如获至宝,德培贤侄一路上手不离卷,到达德州时,已经读过几遍了。遗憾的是只有八十回,他说,一旦此书问世,用不了几日,便有人杜撰《续石头记》之类的狗尾之作;我听此言,觉得有道理——
秋谷问道:“这如何是好?”
赵庆道:“大凡做过这类生意的,手段极是多的!难不倒人的。就拿这半部《石头记》来说;只要人们迷上它,事情就好办了。就象哄孩儿似的,再好的吃食,切不可一股脑儿全给他!只能一点一滴的吊他胃口。所以,大伙儿议论;先抄它一二十回,放出去,多一回也不放的。个把月后再放几回,估计一两年后,全本《石头记》可望出齐矣!我回来时,已经脱手到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就连后半回《贾瑞正照风月宝鉴》,也留待下次接着出手……总之,就这次只出它四五十回足矣!这法子谁都会,只是文人学士放不下脸面……他们都说贾家三小姐贾探春,才是脂粉队伍中的英雄!今天的世道,像黛玉这种人,只有死路一条!……”
秋谷关心的问道:“是否只为赚钱,胡乱抄写?”
赵庆答道:“爹爹放心就是了!冯伯伯后代里,不缺‘贾探春’,现如今只是无钱读书罢了。人穷到这地步,有的自暴自弃;冯家却是小心谨慎,哪敢马虎。”
秋谷道:“你没把真情说知?”
赵庆道:“临走时,冯家非要送我些赚来银子。我怎能收?于是便把爹爹交代的八十两银子,拿了出来,把个真相原原本本道来。据德培的父亲回忆,当年德培的爷爷在翰林院做中书官时,便知曹家口碑甚佳,与康熙皇上如何如何……天地良心,决不乱说,还要当面杀鸡起誓,被我制止……” 想了一会儿,赵庆补充道:“临走我还再四交代,不要张扬,别想一夜变成财主,惹人嫉恨……”
此后,山东颜神镇的‘秋沟’里,又恢复往日的宁静。赵庆日夜攻读,期间德培又来过一次,只不过这次不是步行,而是赶着自家的驴车代步。德培此行专为送上一部刻本《冯舍人遗诗》(雍正十一年癸丑版),说是《石头记》赚来的银子,家人哪里舍得花,就用来把爷爷的诗集刊刻刷印。雕版和纸张都是本地的,虽然差些,倒也便宜,总算了了多年的心愿……
秋谷听得高兴;德培只想多多抄售。按秋谷的意思,先脱手个百八十部,看看情况再说,一时还拿不准。不过那书还只管抄,暂不脱手就是了,再说德州是运河上的大码头,设法把这书售给那些南来北往的巨商富贾和那些乘船客商,百无聊赖之时,正好破愁解闷,用不了几年,江南江北便可传遍。再不,就托人带一部到广州,那里更是传得快
展眼进了乾隆元年。这年乾隆皇帝钦点的是甲辰进士汪由敦为山东乡试座主。原来汪由敦是雍正元年田从典座主顺天乡试时,所取举人;而田从典又是康熙二十三年赵执信座主山西乡试时,所取的门生,雍正初年曾封为太子太师;从康熙末年起,便是当今皇上,宝亲王弘历的师傅。八年前田从典故去。这汪由敦本是鰴商子弟,后入国子监,进士后,入翰林院,职《明史》纂修官,酷爱诗文。因门生田从典关系,赵执信也深知谨堂(汪由敦号)为人。听说点了谨堂做乡试主考官,也就放心了;至少不会因自己被黜而有意刁难。
不出所料,这年秋闱汪由敦录了赵庆为门生。
赵庆中了举人后,并未马上衣锦还乡,招摇过市,张扬一番;而是与爹爹有约:若未中举,就在省城住些时日再返里;否则就去东昌府乘船进京,探望曹家。赵庆选择了后者。
原来赵庆到了东昌府(今山东聊城)得知:据传说当年江宁织造曹寅御使的遗孀还在世,那已经是雍正六年的事了,早就削藉为民,有谁还挂牵?只知住在崇文门一带,一所叫‘十几间房’的小院落。
赵庆到了京城,在崇文门附近找了个客栈住下。刚放下行李,便向夥计打问‘十七间房子’。夥计道::“从这里往前走,过了‘哈德门’,附近有个蒜市口,再打问,没人不知!皇上一天连下三道金牌,就连他家死了几十年的祖宗都封了大官儿……”再看这客官,像是哪门子穷亲戚,前来沾光的。赵庆也不理会又问道:“那家人如今必是耀武扬威的了?” 夥计道:“说来奇怪,这家人家在此住了六七年,左邻右舍竟不知情;今年春上方知这老爷原是江南大臣,贬在这里的。如今是风水轮流转,这不又轮回过来了……” 赵庆也不搭腔,走出店门。
果然,就在菜市口附近,一问便知。那门楼虽有‘一天连接三道金牌’之说,但见门前仍可罗雀。赵庆想起十四年前,在江宁织造府门首的情景,就壮了壮胆子敲门。早有老仆迎接,都是不认得的。曹霑出来,见是一位三十出头的文人模样,不敢怠慢,便请进来说话。曹霑本是个大嗓门的人,早惊动了在母亲房内闲聊的曹,这才认出赵庆来。全家无不兴高采烈。
赵庆在曹家住了几天,先把那《石头记》,已经抄了几十部问世的事儿,当着全家人的面,详详细细叙说一遍。曹兴奋道:“果然不假!我曾做梦,梦见爹爹与一位老者在翻看一部《石头记》小说,正是当年贤弟带走的那一部抄本,记得梦里还质问过……” 李老夫人笑道:“儿自那以后,白日黑夜做的都是红楼‘梦’……”
赵庆道:“爹爹说,他记得家里还有一个评批本儿,那‘无批原本’已经面世,接着再出个‘评阅本’,便顺理成章,天衣无缝的了。按爹爹的意思,先出的那《无评本》只试探出了四十回,看看情景再说;这《阅评本》也先出它六七十回,也不必担心狗尾续貂者。”
曹道:“几年前家母也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便整理了一个‘评批本’,贤弟不妨带去。只是——冠名‘某某评阅’,就难了……我曾想,若冠以‘梦跛斋评阅石头记’字样,不妥;或冠以您家‘红叶山楼主人评阅’如何?”
赵庆道:“更不妥!岂不令人顺藤摸瓜,授人以柄?还是用曹府后人名义,不失真谛,且又隐讳,最佳!”
李老夫人道:“我也一直在琢磨,既然小说写的是‘金陵十二红粉’,必得由闺阁之中的脂粉名义批阅,才是得体!若说‘黑旋风评阅金陵十二钗’岂不亵渎…… ” 说得众人笑得前仰后合。
曹调侃道:“母亲是嫌我当初何不生着女儿身?奶奶也是……”
曹霑媳妇紫烟听了,笑道:“当初我爹妈都盼我是个男孩儿,却偏偏生出个女子来。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要不,我来为叔‘抄批’,便可戏称‘紫烟抄阅石头记’,我这孤弱女子,在外无亲无故,外人八辈儿也猜不出,若出了事儿由我担当!……”
李老夫人接道:“也未尝不可!我也想过,紫烟这孩子来到咱曹家,先是伺候婆婆,如今专门伺候奶奶,就跟我的亲亲孙女一般。这小四合院里如今全靠她操持。紫烟才是真正的‘十七间半房主’;‘紫烟斋’主。依我看,这书名用《紫烟斋评阅石头记》怎样?或者就隐称‘脂砚’斋……”
曹霑欢喜道:“称‘脂砚斋’最妙!”
曹大叫一声:“妙哉!母亲何不早说。” 于是曹便将那羊脂玉胭脂钵的来历故事说与赵庆听。
赵庆如今已是举人,也未曾听过如此典故,赞叹不已。心想,当年曹寅伯伯身处皇室鸿儒才女之间,那梁棠村、孔尚任、洪眆思、吴舒凫、汪渔洋、朱彝尊、宋荦等,乃至冯廷櫆一般的翰林、进士,个个身手不凡;就连家人,虽不见经传,竟不弱须眉,令人起敬。伯伯这《金陵十二钗》岂是凡人可撰得了的?无怪爹爹说过,他遍阅宫廷所藏传奇,无有如此书之奇者!又想到‘脂砚’,忽记起爹爹曾有《藏砚记》一篇,便问道:“家父有《藏砚记》文,其中提过‘南唐砚’,说其‘四方平直’,愿借观,以开眼界,如何?”
曹霑道:“是奶奶答应我的,这有何难?”
紫烟急道:“是奶奶亲手赏给我的,还把乳名‘紫烟’改为‘脂砚’不是?何况这胭脂砚是女人用物……奶奶当初意思是让你转手与我的……” 说着,便回到自己房中,取来一个黄绫包裹。
赵庆接过用黄缎子裹着的一方不大的‘石砚’,果然是‘四方平直’,中间浅浅地碾作一个圆钵儿,白如羊脂,细腻滑润,真精品也!。紫烟道:“可惜磕破一只角儿,可不是我磕的……” 曹霑调侃道:“那只磕掉的角儿,怕是也有一千多岁的了——” 转身对赵叔,诌道:“传说当年赵匡胤灭南唐时,有宋兵在李煜的后宫里,捡到这块白石头,沉甸甸的,只觉得还小了些、也轻了点儿。若不,带回家里腌酸菜做个压缸石,岂不美哉?但不知这物件是个什么劳什子。于是便在那‘雕栏玉砌’上,磕了磕,结果便碰掉一角…… ” 众人大笑。曹霑从紫烟手里拿过脂砚,继续说:“……正在这时,一位军官模样的人走来,见状大怒,夺过那物件儿,骂道,这本是观音菩萨桌上压经用的石头,如何说它是‘杨紫烟’(羊脂砚)的?”
紫烟抢白道:“本来就是奶奶给我的!奶奶还说你小时候就是当年那个宋兵;如今长大了,变成‘宋官儿’了……”
赵庆道:“想不到这磕破了的一角上,还演绎出一卷《五代史》……”
几天之后,赵庆便把这所谓的‘诰命大夫之家’,已看得清清楚楚:家徒四壁,却是万卷富翁!阖家不过淡泊生活怡然自得而已;哪里又有什么‘家道中兴’、‘兰桂齐芳’的景气?(不过是今人为曹霑创作‘红楼梦自传’说所需要的。)便回到房里,取出离家前父亲交代的一个包裹。原是十年前李氏在江宁时送的一包金银首饰,及曹在扬州送的一千两银票,当时说明是抄书问世所用的。哪知秋谷压根儿未曾动用。早准备返还曹家度日之用。如今物归原主。
老夫人及曹见说,不依不饶。李氏见拗不过去,道:“这些金银首饰,路上带着不方便,就留下,我自有用处。” 赵庆恭恭敬敬递给老人。李氏接过,见那包裹竟是十年前自己亲手打的结儿,未曾被打开过。李氏解开,只见金灿灿的风钗,绿油油翠镯,指环儿之属。除了老夫人,都是见也未见,也叫不出名堂的。老人端详片刻,心里一阵疼痛,止不住落了几滴泪水。道:“见到这些物件,就像见到老太后、老太妃们……不过那都过去了,我明年就八十岁了,这身外之物,我来作主,就分给你们几家女眷吧……” 于是便信手分着大小两摊儿。笑道:“执信兄弟家口多,儿孙媳妇也多,这大摊儿由庆儿带回去分分;这副翡翠镯子,是送给我那兄弟媳妇如夫人的,她是苏州人,还年轻——” 赵庆插话:“也快六十岁了。”
李氏继续道:“这小摊儿的,是我偏心眼儿,留给‘脂砚’的多了些。说起来也怪,首饰多了,就不拿它当回事儿。那年隋赫德抄家,拿走那么多,我不心痛,满以为会收回宫里。后来刑部查出那些首饰被他盗卖;我就心痛起来了。再后来退给我五千两银子……”
分派罢了,李氏又取出一张千两银票,抢先说道:“这银子是带给别人的——帮我收下!‘雪芹’(李氏作丈夫昵称)在世时,织造府的银两多补贴了明末的困苦文人,如今,那一辈老人都过世了,下一代人哪里晓得那时的艰难?只说织造府亏空是曹家贪了银两。玄烨心里明白,这才撑到六十一年,雍正便借口先抄了苏州李家……”
赵庆道:“那些年,外面风声紧些,人心惶惶,爹爹不让我乱跑,要不我早该来的。那年到了德州冯廷櫆伯伯家乡,还未敢进京……”
李氏又道:“你家如今也是艰难的,先前那银票你还带回去,自家再置几亩地,或设个私塾,课业子孙;……”
赵庆一听急了,直说不可!不可! 就把今秋自己乡试中举的事说了出来。大家又惊又喜,不可言状。
李老夫人喜得合不拢嘴,忙说道:“有出息!有出息!”说着便把那银票塞在庆儿手中,连说随喜!随喜!接着便对紫烟庆儿等命令似的口气道:“各家把自己那份儿物件儿拿走!谁也不得再提这事儿!”
曹附和道:“老太太是说一不二的!贤弟就遵命吧!今晚设个家宴,为贤弟贺喜!”
席间,李氏埋怨赵庆,中了举人也不先回乡看看。赵庆道:“这也是爹爹的主意。说是这辈子只欠您们家的情。那年在江宁寅伯伯的灵前,许下诺言,回来后便整天家琢磨。五年前冯廷櫆伯伯的孙子德培,从德州步行五百里前来为他爷爷《遗诗》求《序》,爹爹常说,这是老天爷有意安排的,天助!”
老夫人道 :“回去以后,若再见到德培,就让他也来京城看看。他爷爷冯大木我在畅春宫时曾见过,那年大木和执信(读如‘执伸’)兄弟作《诸葛铜鼓歌》,誉满翰林院!当时你那外公汪渔洋,方为诗坛盟主,称赞二人为‘二妙’!康熙皇上也称道不已。谁知如今子孙……咳!不是孩子的错……若是你寅伯伯在,怎么也能扶持些个……带点儿银子回去,你爹爹知道该怎么用的……”
又住了两天,赵庆便要起身还乡。曹已把整理好的一部带有评批及注释的书稿,交给赵庆;那第一卷封面上,已写下:
脂砚斋评阅石头记
赵庆离开京城,不日船到德州地面,就在离冯家最近处下了船。雇了一辆马车,匆匆赶往冯德培家。
原来赵庆因今年忙于秋闱应举,未曾与冯家联络;一年来德培只知京城里换了新皇帝,别的一概不闻不问。家里已经积压了多部《石头记》抄本不敢脱手,正在发愁之际,赵庆赶来。冯家如获救星。赵庆因归心似箭,也不多说,拿出带来的‘新版’《脂砚斋评阅石头记》(‘首评本’),让德培立马用朱笔把那《评批》,按原样儿,过录在一部白本《石头记》上。不下半天功夫便抄得停当。赵庆略看一遍,觉得尚无遗漏;便把带来的原本留下,自己便把过录本带走。临走又留下些银两,交代务必按原样抄写,无论‘夹批’、‘眉批’、‘旁批’,回前回后批,一律朱笔,而且那批处也不得擅自挪动,但是每部不得售足八十回……。德培心领神会。
德培送赵庆到了德州漕运码头,但见人山人海,比那京都哈德门一带还热闹百倍。商贾云集,街上拥挤不堪,真所谓‘比肩继踵而在’,二人看了几处书摊儿,多是售些坊间淫秽话本,倒是《聊斋》之类的散卷、阴阳八卦之书也是不少的,几乎全是手抄本。赵庆打听路人,找了一处大些的书店,浏览一番,甚是满意,虽也多有不齿之作,却也不乏善本。手抄本、刻印本。拓本,五花八门;竟也见到几卷朱彝尊的雕版《曝书亭集》,便买了下来。二人走出书铺,来到另一书摊儿前,德培眼快,拾起一卷《石头记》(无评本),原来正是自己抄写的几回,字迹自然认得的。已经破损不堪,便递给赵庆看,二人会意,必是传阅时失散的,不知怎地又落到地摊上?
二人朝运河岸边走去,赵庆边走边道:“依我看,这《评批本石头记》(首评本),先只卖给南北客商或过往文人,切记见机行事!那些积压在家的旧抄本,也无评批,只卖与市井或一般船家消愁解闷之用。以后凡是大些的鰴商、晋商、陕商只给《脂评本》,抄得要精心,装订要精美——” 德培插话:“价钱要贵些。” 赵庆道:“何止贵些?不过,若遇上穷苦文人、学子,送他一部何妨?往后,说不上冯家发达了,开一处更大的书铺,有自家的雕版、刷印作坊……,想想看,这部《石头记》,也不过试着出了不足百部,本意是完璧流传百世的。只三年,便落得‘妻离子散’的,用不了十年,那出手的几十部怕是不见踪影的了。只有精本,若能做到一卷难求,即使要它再多的银子,也会有人收藏的。若像眼下这般,凭一时之兴趣,阅过之后便不再理会,待到后来人想看,也找不出个完本来!咱们还需仔细琢磨……”
赵庆登船时,小声对德培耳语道:“明年春上之前,我要做些准备进京会试去碰碰运气,没空儿……” 德培一听,惊得目瞪口呆。赵庆已转身登船,德培还呆在岸上,半天才自语道:“就连给举人老爷叩头的空儿也不留的……”
话说到了乾隆二年,京城的曹家、德州的冯家,无不望眼赵庆。直到会试、殿试结束,仍不见踪影。原来赵庆中举回来,只把那心思放在了进士上,苦读寒窗一冬,正准备收拾进京赶考,便病倒了。本来是乡试座主汪由敦推荐的得意门生,早不病,晚不病,偏偏在就这个节骨眼儿上一病难起。家人岂能不急?无可奈何只能听天由命的了。到了五月里,秋沟山里转暖,赵庆病愈。赵执信夫妇这才缓过气来。本来赵执信最是痛爱其六子庆儿,责无旁贷地悉心教诲,实指望庆儿走这仕途,堂堂正正地做个心目中的良臣。看看眼前这情景,秋谷那如夫人死活不让儿子去考进士了,说是上天有意让庆儿考不取的,若不会那么巧?;秋谷的功名仕途之心,也就早已凉了半截。细想自己十四岁补博士弟子,十七岁中乡试第二名举人,十八岁中二甲进士,入了翰林院。二十八岁便因演了一出戏的屁事儿,被革职回乡。古人说得透彻:【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三国时魏国人李康《命运论》语)。浊世之中,何谈清白?江宁织造的曹寅兄,可谓清白一生;然而,皇太子当面索金,哪个敢不从?李煦岂敢不为皇子胤禩强买苏州女子?赵庆儿既无曹家之势,也无寅煦之能;虽有汪由敦极力推荐,又有常熟名儒仲翰村调教,凭庆儿自己的才华,得了进士,难保善终的!人非圣贤,岂能无错?如其届时后悔,不如早退一步。想那南宗五祖有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尘世之人能如此者,足矣。若如六祖所云:【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岂不是神仙了么?宝玉说的‘无可云证,是立足境’。人在红尘,当有立足之地;若如黛玉的‘无立足境,是方干净。’那位六世佛祖惠能,只有圆寂方是干净的了……
于是,赵执信老着脸皮给朝中的汪由敦修书一封,婉转地谢绝谨堂大人好意。谁知次年春上,谨堂来信,言称:从吏部得知,河北沧州县令丁忧回江南去了,不知幼石(赵庆字一,又字‘万君’。)贤弟可否暂代几年?事后另谋佳职;如允,从速来吏部领命,云云。秋谷一家大喜过望,赵庆更觉得沧州临着京杭运河码头,又在京城、德州之间,古来虽是发配之地,事在人为。若终生不迁,只为此令,也是值得的。
不久,赵庆主仆二人启程赶赴京城。一路上,赵庆踌躇满志,济南府、东昌府也未曾停留。及至上了运河,忽然想起前年李老夫人嘱咐,想见见大木的孙儿德培。于是便让船家在德州停了半日,主仆二人匆匆赶往冯家,言明来意,说是一起到京城,认认曹家门。德培原本就想进京见识一番,以后不免要来京里联络推销《石头》,只是眼下衣衫破旧,羞见曹家。赵庆不容分说,便催着德培上船再议。
不几日,船到通州码头。赵庆本想带德培在通州熟悉一番,因公事在身不敢耽搁,便来到京城。此时汪由敦刚升迁内阁学士不久,值上书房行走,兼做皇子的师傅(后为太子少师,太子太师,刑部尚书登。)。已是内阁之中的佼佼者,近因奉旨外巡,走前已与吏部谈妥,并留下话来。因此吏部手续不下两个时辰便办得妥帖。原来这书办是一位笔帖式出身的旗人老者,得知眼前这位后生便是当年被革职的年轻翰林赵执信的六子时,叹道:“您家老爷子是条好汉!敢作敢当,就连旗人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旗人祖上多是武出身,最是尊崇义气……” 赵庆道:“好汉不提当年勇,爹爹至今还常说当年好心做了错事,为皇上惹下麻烦,说自己对不住康熙皇上……”
赵庆离了吏部,便与德培急忙赶去崇文门外菜市口。
只因公务在身,赵庆不敢怠慢,只在曹家住了二日,便打算先去沧州,略事安排一番,然后回到博山接眷属来沧州。留下德培暂住在十七间半房, 嘱咐多在京城街头巷尾及庙会等处走走看看,广交坊间朋友,为以后准备些出路。李氏八十一岁,年事已高,对《金陵十二钗》的事儿也就渐渐放下心来,由着下辈人做去。曹与赵庆商妥:此后《石头记》的‘脂砚斋评本’由德培操心,经由漕运水路,先往南传售,暂不进京。临行前,曹将一部写有更多评批的底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交给赵庆,道:“此‘再评本’,带回,请赵叔过目增删。待到‘首评本’传抄几年后,不妨的再改用这个底本(令人不知首尾)。只是将第十三回《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做了些改动。我觉得秦氏其人,岂是安荣富贵之人?对王熙凤的一席托付之梦言,令人悲切感服,不忍心贬之。那《遗簪》《更衣》诸文过于露骨,应以隐写为好;何况秦卿之过,乃贾珍淫威使之。故令天佑改写为《秦可卿死封龙禁尉》(暗渡陈沧之法。)。我把这事儿记在此回回前,只因说到‘天佑’之名,似不妥。今说与你知,请赵叔或是贤弟定夺。”
及至秋谷见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时,觉得 曹大有长进,曹天佑改写的一处,也是不凡手笔,心里甚是赞叹:即兴作七绝一首,顺手写于此回前,云:
生死穷通何处真?英明难遏是精神。
微密久藏偏自露,幻中梦里语惊人。(《红楼梦》第十三回,回前诗批。)
兴奋之余,突发灵感奇思:寅兄一家三代,虽无状元进士之功名,真乃西天‘三生石畔’之仙圃——‘曹圃’‘芹圃’也;‘灵河’万溪之一溪——‘曹溪’‘芹溪’也!非此,如何能把个‘神英侍者’、‘绛珠仙草’看得真切、透彻?如此方能‘幻中梦里语惊人’!况且‘仙圃’之中无良莠之分;‘灵河’之溪无上下之别!管它雪樵、雪芹。芹溪、芹圃。均是圃中之苗、溪中之水。玄机不可泄露,为的就是让世人混猜去罢!于是将此奇想说与庆儿,赵庆口服心服,心想‘生姜还是老的辣’,‘唯恐天下不乱’……
列位看官;说书人看来,赵执信这一‘损招’害得世人叫苦不迭 !爷爷曹寅有号‘雪樵’,孙子曹天佑,号‘雪芹’;不管他‘雪’字有悖常理与否,说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却是无争议的。谁知几世几劫之后,有好事者,非要查查这曹雪芹的履历;有位名曰‘俞平伯’的人,说什么,
【文学的背景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真正了解一种艺术,
非连背景一起了解不可。作者的身世性情,便是作品背
景的最重要的一部,我们果然也可以从作品去窥探作者
的为人,但从别方面,知道作者的的生平,正可以帮助
我们对于作品作更进一层的了解。】
于是‘雪芹’、‘芹溪’二名,是一人?或二人?有势大人多者,便把《红楼梦》的著作权给了曹寅的孙子——一位少年天才作家——曹天佑,字霑,伪号芹溪,芹圃者,此人便是‘曹雪芹’。也有人并不认同;从而引起一场‘百年红战’!是耶?非也?‘主流’也?‘逆流’也?还在混争不止……
书归正传。到了乾隆五年十二月,赵庆代职期满,安排家眷先回济南府,只身回京交差,深得吏部赏识,便被任命到江苏吴县做了县令。赵庆满心欢喜,能回母亲的娘家苏州府地做官,做梦也不曾梦到的。必是汪由敦的苦心,把一处就连进士也难得的去处,给了自己的举人门生。正准备先往拜谢,而后再去菜市口曹家。就在十九日这天,曹霑赶来宾馆,跪在赵大人面前,哭道:“奶奶今晨子时归天了(享年八十三岁,与曹寅雪芹同年所生)……”
就在曹家忙于李氏老夫人丧葬之时,曹提出一个思考已久的曹姓家族的大决策:时值寒冬腊月,不妨先把母亲入殓,停灵家中。原来江宁曹家本来曾打算在江南购置一处莹地,只因江宁织造连年入不敷出,一拖再拖,直到家被查抄,也未成行。这才想起祖籍丰润。于是派曹霑立即起身前往江宁,将祖父曹玺、祖母孙氏,父亲曹寅及哥哥曹颙的遗骨运回;最快也须在明年三月运抵京东通州。待到过年二月,再将母亲李氏、嫂嫂马氏的灵柩运往通州等候,六口棺木会齐了,一并北上丰润,入土为安……
计划停当,因是曹姓江宁一支自家的事儿,且是今非昔比的,也就无需张扬。曹天佑带上仆人,雇了一艘快船,与赵庆同船,日夜兼程南下。不几日船到东昌府,赵庆下船,赶在年前到家,不表。
话说天佑的快船正月末便到了江宁。只与官家说知,将厝在江宁名宦祠附近的曹玺灵柩与厝在郊外古刹中的孙氏及曹寅、曹颙灵柩请到一艘民船上。因是三五十年前厝在江宁的,如今曹家衰败,也多不被世人记得的,再加上曹家本就不愿张扬,如今虽虚有空名,也不想让今之人回顾已散场的往昔盛宴。似是人不知鬼知,顺顺利利地离了曾是曹家三代人苦苦经营了六十余年江宁织造所在地,徐徐北上。曹天佑倒是觉得本是一件无所谓的事儿——天下黄土何处不埋人?只有那一家三代四口的幽灵,迟迟不肯离去,直到运灵的船只过了古陵驿觉迷渡口,方急急地跟上船来,随那枯骨回归故里……
到了二月底,曹便陪同母亲、嫂嫂的灵柩先期到了通州。不久南来的灵船也抵达通州。不费周折,也无仪式,一排六口棺木,曹玺灵柩在前,浩浩荡荡望丰润而来。
只因江宁曹家一支,只知远祖为丰润曹氏,大明朝时移居或驻守关外,明末时,关外曹氏后人多入了旗藉。清初曹寅的曾祖曹锡远‘从龙入关’,当为有功之臣。因已入了旗藉,又因年代久远,虽与丰润曹氏断了宗谱,却不忘自家是丰润曹氏后代,只是尚未‘联宗入谱’,本地曹姓(国初汉人仇清,丰润当不例外)是否应允旗藉曹氏联宗,暂时不得而知。曹此行,心里已经有数,‘联宗’之事,一时难定。于是在正月里便派人到丰润,交代在曹姓祖莹以北,圣祖康熙皇帝的景陵(地处丰润北遵化境内)以南的丰润境内,选一小片荒地,用不了多少银子购置下来,作为祖父曹玺一支的莹地。南面丰润曹氏祖莹,北望遵化康熙皇上景陵;既不忘祖宗,又不忘皇恩,乃天意也。既不可让先人久厝在地上,先入土为安方是当务之急。眼下既不立碑,也不刻铭,待到‘联宗入谱’事成再说。即便不成,总是落叶归根的了,葬于此地,本地曹姓既管不着,也无理由不允的;此后不知何时,终入《五庆堂曹氏宗谱》,不表。
看官:有道是此回演绎《红楼梦》成书,如何大谈曹家葬经?说来也奇,自从《红楼梦》问世,世人追根问底之癖日盛。遗憾的是‘曹雪芹’何许人也?尚无定论,‘掘墓寻芹’之风在所难免,何必再去打扰那些生前提心吊胆的枯骨?似不可取!回顾康熙四十八年朱彝尊辞世,也未葬在其曾祖、大明万历英武殿大学士朱国祚百花庄墓地;而十七年后雍正登基,竹垞葬在五里之外的一处新茔。那时曹尚在江宁织造任上,必知其意。似有与大明‘划不清界限’或‘避嫌’之虑。何况江宁曹家仍是旗藉。古今类同!
葬毕。孙氏及其‘雪芹儿’有了安身之地。况且此处距康熙景陵寝宫不足百里之遥,虽分属遵化、丰润两位‘土地爷爷’管辖;母子二人,有时带上儿媳李氏常到遵化寝宫走动,看望孝庄、顺治,更多则是与玄烨说些往日趣事。李氏当年对雍正不满,赌气要找玄烨说理的事儿,早已忘却的了;‘雪芹儿’则隔三差五的独自前往景陵,或与玄烨独聊;或与远道飘来的‘青格儿’对泣;有时三人一起又谈笑风生,不知何故?圣祖玄烨吃腻了享殿里的祭享,也常跨境到丰润来尝些曹家后人供献的粗茶淡饭,丰润一地的土地爷爷也就习以为常,从不为难……
此后几年,京城菜市口的十七间半房内,倒也安然平静,而少些生气;德州的冯氏子孙则忙忙碌碌,日子也日见宽裕;只是到了乾隆九年,远在山东博山的赵执信 秋谷已是八十有三,一病不起……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2009-5-28,端午 一稿
2009-9-5 修改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康熙朝曹寅才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