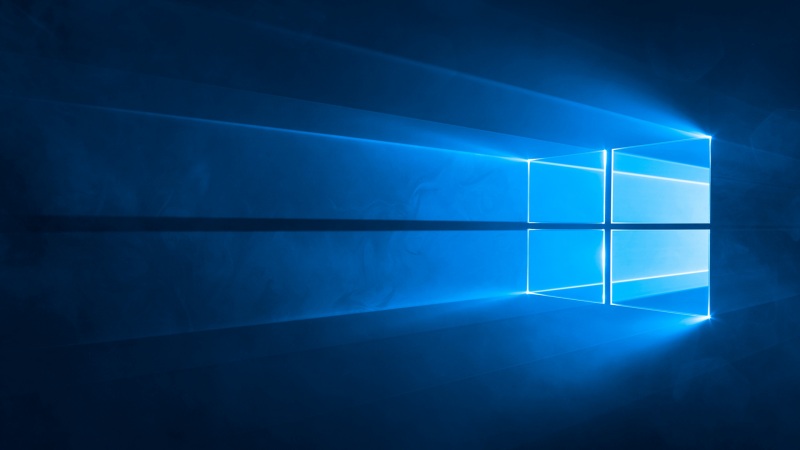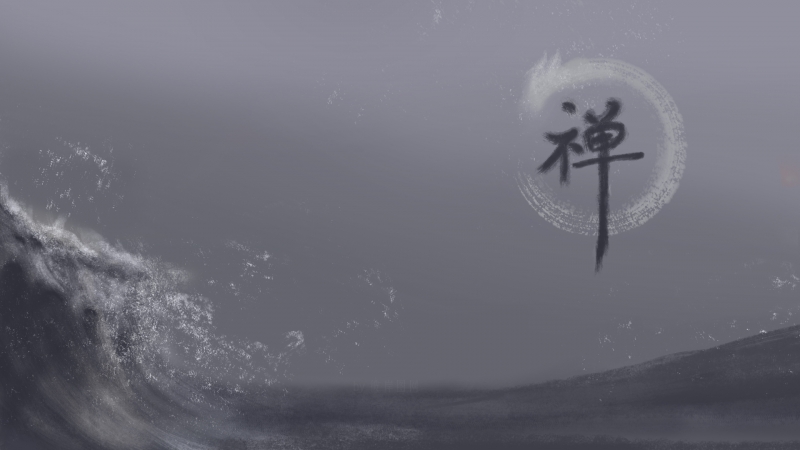提示:本文共有 10988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22 分钟。
3 月 24 日下午,“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启动仪式暨论坛在北京的 CHAO 酒店举行。
该奖由出版公司理想国和瑞士钟表品牌宝珀(Blancpain)联合主办。首届评审委员为作家阎连科,作家、《上海文学》执行主编金宇澄,文学评论家、作家唐诺,学者、文化评论家许子东,音乐人高晓松,涵盖多个领域。
主办方称,首届参评作品应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期间,在中国大陆地区以单行本正式出版发行的简体中文版小说作品。凡用汉语写作的长篇小说或中短篇小说结集均可参评。不接受多人作品合集、选集。评委会成员每年更换。现正式开放作品征件,最终获奖结果将于今年 9 月揭晓。
在启动仪式上,“看理想”策划人、评奖办公室负责人梁文道这样解释设奖的初衷:“我们希望能够为中国的文坛,特别是在小说这块领域,带出一些我们认为非常有潜质,有一个长期的创作的自我预期跟动力,而且有相当成就的一些作者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让更多的人欣赏他们的作品,这是整个奖的根本原则。”
梁文道
而相比国内的其他文学奖,“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最大的特点是限定参评作者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以作品出版之时作者年龄为准),而这给了年轻作家更多的机会。
许子东在媒体群访环节就称:“现在评奖为了保险,都是给大牌作家。这批人从寻根文学到现在,统治文坛 30 年。他们的确有很多优先的条件,有文革的经历,知青的背景,而且 80 年代西方的写作技巧进来,其中一些人还特别勤奋。一个王安忆,一个贾平凹,你赶都赶不过来。这篇没看完,下一篇又来了。”
“现在最缺席的是评论界,我们这个行业在当代是最不称职的。为什么呢?评论界没有批评,没有流派。所有的评论都是被出版商操控的打书,而每一个作家旁边都有几个好朋友的教授。书还没有卖,这些教授就已经写文章了。你看《匿名》,大家都还没看,陈思和他们已经有文章把王安忆说得多么好了。”许子东补充说道。
另外,“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获奖者只设一名,奖金达 30 万元。相比中国大多数文学奖只有几万元的数字,这个数字算是丰厚。官方文学奖奖金最高的是茅盾文学奖,奖金达 50 万元。民间文学奖中,去年设立的“京东文学奖”的最高奖金达 100 万元,这也是国内文学奖的最高奖金额度。
除了奖项的介绍, 5 位评委还以“不悔少作”为主题各自做了演讲,回望了自己最初的文学历程,并朗读了自己的“少作”,最后还接受了观众和媒体的提问。我们把这些演讲和回答选取部分摘录如下,希望对你有所得。
5 位评委及主持人梁文道
演讲和问答部分摘录:
阎连科:
我非常懊悔自己一生的写作,80%是垃圾
我非常懊悔自己一生的写作,今天去看少年的写作会呕吐出来。为了下午发言,吃饭的时候我又拿出少年的作品看了一下,饭都没有吃,差一点让我们全家人饭都吃不好。但是毕竟来了,还是要讲。我确实没有不悔少作,我经常讲我一生写了非常多的作品,其中 80% 是垃圾, 20% 比较好,但这 20% 有多强的生命力?我活着它就活着,我死掉它就死掉,我死掉这些作品也就没有人提了,那 80% 没有人提的作品,确实是垃圾。再往前推,说到少年写作,我先给大家讲一下,你们都会觉得真的是垃圾中的垃圾。
我最早是 20 周岁当兵,“天才”般发了一个短篇小说,叫《天麻的故事》,发在原来的《武汉军区战斗报》上。故事讲的是一个士兵特别想入党,当然要表现好,还要给指导员,也就是党支部书记送一点礼,就给他送了一斤天麻。指导员也非常开心,把天麻给送回来了,又写一封信,要入党你要如何表现,不能送礼。如果这个少作写得好的话,那它就是正能量、主旋律的鼻祖,我在三四十年前就比他们写得好,这是我不悔少作的一面。
当时我是初中毕业,拿了一个假的高中毕业证到部队去,他们说这个人最有文化,发了一整版的文章,全军都在轰动,给了我 8 块钱的稿费。那个小说编辑部还给我写了一封非常好的信,说你这个故事非常非常地好,但是你的风光描写比那个故事更好。他们不知道,我之前从来没有读过外国小说, 20 周岁以后第一次读了外国小说,读的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的短篇小说《白净草原》,那个风光描述如此之好,语言如此之好。现在说我抄袭可能有点严重,说模仿又有点对自己简单化地处理,介于抄袭和模仿之间,对这件事情我不可能不懊悔。
阎连科
莫言和余华“少作”写得好,因为他们早就看过外国文学
我一直在反省,为什么莫言就写了《透明的红萝卜》,余华就写了《十八岁出门远行》,阎连科就写了《天麻的故事》?这件事情我一直想啊想啊,最近就想明白了,原来是 20 周岁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过外国小说,他们居然都看过。 20 周岁以前我在乡村看的都是《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三家巷》《铁道游击队》,我倒背如流。这些小说不是不好,而是好到让你无法去学习,当你生硬地去学习的时候,就会写出不好的小说来。到 20 周岁以后,偶然当了图书馆的保管员,要找一本外国小说去看,找最好的。哪个最好?《飘》最好。它的封面是特别美的一个明星演员,《乱世佳人》的费雯·丽,她在封面上,那当然要看这个小说。上中下三本,用三个晚上看完,天下还有这么好的故事!中国的革命小说虽然好,居然这个革命小说比那个更好。它也是写战争,也是写爱情,也是革命加爱情的故事。从此开始读外国小说了,从此发现小说写得不如以前了。
我就是这么一路走来,几乎一生都是特别的懊悔,所以我想没有不悔少作。到最近一直在写作,我想我全部都是在懊悔中写作,唯一没有懊悔的就是你非常勤奋,非常努力,但是每一部小说留下的遗憾都超出我们的想象。
这是我的中篇处女作,写的是战争的故事,虽然我没打过仗——我差一点去打仗——我对战争的体会可能超过那些去打仗的人。这个小说叫《小村小河》。我第一个短篇小说挣了 8 元,这个中篇就挣了 800 元,给家里买一个电视机。我母亲拿着这个小说数多少页,她说居然写这么一点东西就能挣 800 块钱,这个事情还是可以干的。那我一生就按照我母亲说的这么干下来了。这个中篇是在第一篇小说的五年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发出来,过了三年以后终于发出来了,那是个非常漫长的故事,我回头一看充满了激情,里面有好多诗歌。
第一首特别好:有河就有村,有村就有河。村是河的家,河是村的歌。
第二首诗:七姓窝的七户人,清明上的七个坟,开门种了七家地,关门揣了七条心。
第三首是“五讲四美”的:娘养儿一天一年恩,儿给娘买盒抹脸的粉;娘养儿一年十年恩,儿给娘扯条围头巾;娘养儿十年百年恩,儿给娘扯条送终裙;娘养儿二十恩不尽,求儿把娘送进坟,坟前栽棵不老的柏,记住娘养儿的一片恩。
写的时候我都掉泪了。写得太多了,我随便挑几个。
铁桶的江山我来打,铜铸的交椅你坐成,只怪我麦黄没官命,只怪我豆大的字,不识一个两个。
东西南北中,征战一股风。打过蒋介石,砍过日本兵。老子是好汉,干儿是英雄。国家南门口,有个二罗成。
金宇澄
在东北下乡七八年,我一度以为自己是个东北人
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在文革阶段, 16 岁多一点到东北黑河这个地方,就是下乡。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地方就像契诃夫的《萨哈林岛旅行记》,黑河地区的特殊农场,因为 1969 中苏关系紧张,大部队迁走后,仍然留下了很多刑满人员,所以我整个的成长阶段,我下乡干的所有农活,都是这些 10 后、 20 后、 30 后的特殊身份、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人在教我们怎么劳动。
我有个高中朋友在上海,他没有下乡,我们俩经常通信。他看了很多很多的书,我记得在 1967 年的时候,他就在看《小逻辑》,看叔本华,我跟他特别合得来,整个青年时代,我们俩都没写过东西,都是写信。一次他给我回信说,你是可以写小说的。但当时真没这环境,整个宿舍双层板铺,睡七八十个人,非常吵闹,最多只能写信。我也跟他说,他完全可以写小说,但我们都没有写作。当时也有一些农场的青年喜欢写作,但据说如果要给《黑龙江日报》写篇稿子,要政审,要有本地革命委员会开的介绍信,我因为出身不好,根本不可能会有这个想法。直到我 8 年后回上海, 30 岁后总算生活安定下来,才开始写东西。但那个朋友 80 年代初去了美国,他是个特别聪明的人,一直不写东西,现在想想真是可惜。
我一直觉得,自己得有七八年时间在那边生活,我的根就在东北,在 1985 、 1986 年写了几篇这方面的小说, 1988 年调到了《上海文学》,原因是参加了作协“首届青创会学习班”,写了个获奖小说,孙甘露也在这届,他加入时已完成了《访问梦境》,我一直没交东西,直到最后结束阶段,连夜写了个东北棺材匠的故事。当年那地方的规矩是:如果当晚有人要死,就通知做棺材,没想到连夜做了棺材,一大清早病人却活过来了,这口白皮棺材就搁在木匠房外晒着,此后,场子里一直没死人,棺材风吹雨打,越来越丑陋,大板缝,呲牙咧嘴,甚至有人在里面养鸡鸭。但是所有身体不好的老人都偷偷过来看这口棺材,因为规矩就这样,接下来谁死就得用上它,最后是两个老人同时弥留,但都干耗着就不死,小说结束在这地方。
金宇澄
年轻人一定要想办法试着做各种事,熟悉身边的故事,想办法写
我到《上海文学》后也写了一点,现在说就是“少作”了,都是三十多岁才开始写,比如《方岛》, 1963 年的割麦竞赛,千米之外的麦子地里,放一板桌,一天的口粮就搁在上头,谁先割到桌子就随便吃——这是我学泥瓦匠时,我广东师傅回忆的,说如果是你们上海人或北京人,他肯定是活不到现在了,实在是干不过那些割麦子的同伙啊,年纪都比他轻,但是他发现了麦地里有不少刚出生的小耗子,在当年他眼睛里,就是麦地里的广东虾饺,粉嫩的、粉红的,他天天就偷吃这些,活的吞下去,用一个布袋子收集起来。
我做编辑后,就写得很少了, 16 岁到东北,在写作上,我变成一个东北人,总有这错觉,直到近年写小说,才发现了我到东北劳动了七八年,实际没有接触到真正的中国农村,受的是“特殊教育”,是这些特殊人员给我的内容,我没有真正接触到“贫下中农再教育”。与此同时,我和那位在美国的朋友已没有多少来往了,他出国后变得孤僻,我一直期待他可以写小说,但他做了生意,也发生一些生意上的问题,来上海基本也不联系我了,有一次我再三跟他说,我跟生意没任何关系,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啊。但我们就没有来往了,直到 15 年我得了奖,有一天下午,我在传达室看到一封信,是他给我的信,一看知道是他的字,里面就写了一句话,祝贺得奖,没有落款,他已经根本不想再联系我了,我整个青年时代经常来信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一个年轻人,一定要想办法试着做各种事,熟悉身边的故事,想办法写。我现在想想很后悔,当年在东北认识那么多 10 后、 20 后、 30 后的男人,当时都没有记录他们下来的故事,只是随便听他们说了一些。有几个广东师傅后来都特赦了,记得是 74 年国民党县团级以上都遣散吧,集中排着队,拎着统一的旅行袋就走了。
我一直觉得,我的根在东北,恐怕也是我的遗忘,是写了这些,很久以后才有的醒悟,最熟悉的生活,是我 16 岁前的上海,少年时代对每位作者都那么重要,我却要等到接近 60 ,才写了关于上海的《繁花》。我现在读这篇“少作”的结尾部分,《不死鸟传说》,发在 1993 年的《收获》上。
“待我们走到了慢坡的最高处……此刻,我们立刻想到了大春,想到了美芳和根娣,感到了极其的寒冷,感到神智错乱,看着不远处的这个模型状的小孩,浑身那一块鲜亮鲜红的色泽,我们口中只是喃喃自语: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搞的?!”
唐诺
文学书写大概不是一个太早慧的行业
我讲一下我个人的书写经验。我其实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因为如果书写的成果比较好的话,还能算是一个还不坏的励志故事,但是因为书写成果的关系,所以算一个反面的例证,也跟大家说一下。
我大概是在 14 岁就没有怀疑过自己是希望在书写的世界、文字的世界里,真正开始有意识地写作大概是 18 岁高中毕业,跟朱天心、朱天文等一批朋友。当时因为机缘的关系,我们就办了一个文学杂志,所以从大一开始就一面读大学,一面办杂志,开始有意识地写作。
但是,我真正写出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应该是在 45 岁,叫《文字的故事》。虽然写得很糟,但还算是一个完整的作品,中间相隔了大概 27 年。这 27 年间倒也一直在写,但所有的作品我都没有存留,所以不是一个好的例子,在谈少作的时候,我的成果非常非常糟糕。
我也自己回过去想这个事,除了我自己的书写资质比较迟缓,学习比较鲁钝以外,也会为自己找一个理由,可能也是真的,我觉得这里头还是有个基本核心事实,我觉得文学书写这个东西,大概不是太早熟太早慧的行业。我比较相信文学是一个专业,一个专业必须要有时间,必须要有长时间的学习跟锻炼。任何一个专业要做出一点样子,要出师,都需要一段时间。尤其现在文学的专业性越来越不被讲究,起码在台湾是这个样子,我开始慢慢强调较为专业的部分。
尤其今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重点是小说,诗还好,像梁文道也提到兰波甚至是拜伦、雪莱、普希金,他们的巅峰来得比较早。我以前有一篇文章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诗的早熟可能来自于诗的唯我性,甚至“我”必须带着某种吞噬性,某种非常霸道的呈现,适合年轻时候的从身体到心理的状态,所以诗的巅峰来得相当早。但是小说不是,小说的“我”不是这个样子的,依我看它是一个小写的我,那个小说的“我”必须要放在时间里,放在人群中,它必须跟这个世界相处,必须要知道理解很多东西,要比较沉静地一样一样去发现,需要去感受,去获取,去证实,去了解。所以依我的看法,小说一般的巅峰期不会来得太早,应该会在 40 岁以后, 45 岁以后,他才慢慢走到书写的巅峰期,当然这个都有例外,大体上它的高峰期是这个样子。
唐诺
文学是最孤独的行业,博尔赫斯的少作也很差
台湾有很多文学奖,大陆也是,我是欢迎的。文学奖的重大意义在于,我们需要有不一样的奖惩系统,因为如果没有其他的奖惩系统加入的话,最终我们会剩下单一的奖惩系统,就是市场,以数字来决定。所以文学奖的设置,让我们在市场的数字之外,还有可能诉诸文学的专业,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几个月前,我在上海跟王安忆一起担任小说评委的时候,我记得她说,毕竟这样的场合不是文学的基本事实,而是一个嘉年华。文学没有这么繁荣,没有这么热闹,大部分的时候它是非常孤独的。以台湾的标准来讲,它甚至是非常清苦的一个行业。我很怕年轻人误解,以为这样的场面是文学的常态。文学大部分时间只有你跟你所写的东西,马尔克斯曾经说这是一个最孤独的行业,他形容这种孤独不是在孤岛上,而是落水的人在跟大海大浪搏斗,只有你自己,谁也救不了你,这才是文学的常态。
我的少作糟透了,拿出来的话对大家身体不好,所以在这里我就跟大家讲两个简单的事,作为一点点补偿:
一个是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他的第一本诗集据他自己说是他父亲花钱印的,后来当他正式出了自己的诗集之后,他就逐家拿自己的新诗集去跟对方商量,能不能把我那本换回来,打算把它消灭。
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在台湾,大概二十年前我曾经有一个无聊的想法,突然想出一本小说集,因为我认识的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这些人,他们都是早慧的作家,二十出头就已经名满天下,我知道他们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哪里,是哪一篇。我想征求他们的同意,把他们的第一篇小说收集起来,出一本小说集,那时候我连文字都想好了,大概是说如果你想写小说就放心写,你看他们曾经都把小说写成这样,你还怕什么呢!
但因为张大春不肯就范,所以这本书就没有编出来。张大春第一篇小说的名字,我不敢在这里讲,如果我说出来,他会跟我绝交。他已经威胁过我很多次。大概这是太早写小说的人的事实真相。朱天心写第一篇小说时 17 岁,叫做《梁小琪的一天》,现在看当然非常糟。朱天文叫《强说的愁》是在中山女高二年级的时候写的。
许子东
我是一个最普通的知青,我都可以抗掉这个诱惑,你们为什么不可以?
我出过十几本书,但是都是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我还发表过十几篇小说,我的文学成就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公正地对待。
画面就是多年前走进上海文学那个楼房,我到现在还记得,《上海文学》的那个楼是非常西洋化的楼,那个楼梯旋转下去。他们刚才讲了文学的寂寞,我现在讲讲文学的另一面,它可以说明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政治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当时已经是华东师大的研究生,《上海文学》说收到说这个稿子可以修改,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因为我们的华东师大只有三个人是作协会员,赵丽宏、王小鹰、孙颙,(但)我的创作比这更早。
第一次有人讲我可以创作,是在我 15 岁下乡的时候,看手抄本。当时一本本是油印的,叫《少女之心》,另外一本不知道什么名字,但是前后都已经翻乱了,也不知道作者。两本书的特点都是里面写到胸部、大腿,我们是带着看苍井空的心情在那里看。看完了以后,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油印的《少女之心》一般,另外这本比较好。他说,我们也可以写。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我们也可以写。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本被翻得一塌糊涂的书,是茅盾的早期小说《幻灭》。当时我们对他不尊敬,我们是带着看黄色小说的眼睛去看他的小说的,所以我后来做现代文学研究就带着赎罪的心理,茅盾居然写了这样的作品,我的意思是我们当时不懂。
第二次那是认真的,我插队的地方除了知青以外,还有南昌下来的干部。这个干部知道我有点喜欢文学,劝我写小说。我写了,但就跟金宇澄刚才讲的一模一样,《江西日报》居然给我回了一封信。我后来才知道,在给我这封信之前,已经有了政审。到我的公社,查许子东这个人怎么样?通过了!我的公社书记非常高兴地跑来跟我说,《江西日报》给你来信了吧?你们怎么知道了?他们说,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都说你怎么怎么好。
今天你不能明白,如果在 74 年的时候,我已经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的话,我在这个公社的地位就彻底改变了。因为那个时候报纸只有几版,我一登的话就是大半版。但是,他给我提了一个修改意见。这个修改意见简单地说,我本来是批评招生被中断,知青在农村的无奈,他要把我的小说整个拧过来。
这是我一生比较重大的决定,我当时没有太多的想法,我也不信宗教。那个时候,我的世界观也没有形成,但是我有非常朴素的一个想法,我到现在还坚持这个想法,就是一个人可以在很多地方说假话,可以在节目里面,可以在男女谈恋爱的时候,可以在做生意的时候,但是一个人不可以在自己的作品里明知道是假的,还去说假话。
因此,我就丧失了这个机会。我肠子都悔青了。要不然的话,我的作品就应该出现在《朝霞》上。你们不知道《朝霞》当时有多大的意义,我后来在《朝霞》上看到了很多我现在文坛朋友的名字,他们早早地在文革中期就开始写作了,而我错过了这个机会,以至于后来发表小说推迟了五六年,我的文学地位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我一生经过这样的选择不多,经过那一次选择以后,我后来听到有名的人,类似地讲那个时代怎么怎么样。我不相信。我是一个最普通的知青,我都可以抗掉这个诱惑,你们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在一个时代面前,为了好处就可以说一些这样的话?我不原谅这些人。
这篇小说后来我又寄给巴金,居然他给我回信了。回信就是说,我有个亲戚是编杂志的,我不做评论,我转给他,谢谢你信任我,许子东同志。哪怕是文革后,后来编辑给我回的信,也还是要我修改。
许子东
我一辈子写的东西不多,但是好在都不需要怎么改
我后来写了一篇小说,发表在《百花洲》上,稿费 120 多块。我在农村干一年,除了口粮以外是 76 块。一篇小说一个礼拜就写成, 120 多块。这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就像阎连科说的,这活可以干。但是,前面有一条,写小说不是那么私人的事情。
我后来写了一个小说,讲的是真事。我们很多人都喜欢一个女知青。她的哥哥是给我们看《基督山恩仇录》、罗曼·罗兰,一个非常有文化、弹钢琴的。可是,他居然把他的妹妹介绍给公社干部,在一个招待所里做事情。在我们看来,觉得是一个堕落。我就写了一个小说,题目叫做《可怜的人》。在小说里,主人公对她的哥哥表示非常愤怒。怎么能够把你的妹妹,明知道陷她于不义,还这么做?!
小说发表以后,正好同一期看到王安忆的小说叫《绕公社一周》,也写了一个很会混的、很会搞关系的男知青,但是我写的是主人公鄙视这样的人,表达我真实的感受,而王安忆小说的主人公是羡慕那个混的男知青。我的同学王晓明跑来跟我说,子东,王安忆这篇写得比你深。这个人很糟糕,见风使舵,为了利益,为了一点好处放弃自己的价值原则,但是主人公要是鄙视他,他认为就浅了,主人公还得羡慕他。我的文学道路就这么被他们中断了,让我印象非常深。
我的老师钱谷融先生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我一辈子写的东西不多,但是好在都不需要怎么改”。你们要是知道他从 50 年代发表《论文学是人学》,60年代因为《<雷雨>人物谈》,他们在上海作协开会 67 天,天天批判他们,开会下来,文章不改。所以,我能向老师学习的就是这一点,写的东西也许不好,也许不多,但是将来也不需要改。
高晓松
“艺”是那个门,“术”是门里面的魔鬼
少作我肯定是不悔的,我要是悔少作,就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因为我发表的第一首歌就是《同桌的你》。我今天的一切,今天能够腆着脸站在这里,其实都是从那儿开始的。当时的目的并不是发表,或者出唱片,就是给女生唱歌。当时的目的都达到了,每一次弹唱都有点收获,所以肯定是不悔的。但确实今天回头看,怎么每句话结尾都是你,从歌词上来说,确实显得很粗糙。
艺术这个东西其实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艺”,就是唐老师说的专业性;然后是“术”,就是你心里那个世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那块地?那块地长出了什么东西?这两个东西我打一个比喻,我自己写的时候有明显的感觉,“艺”是那个门,“术”是门里面的魔鬼。
年少的时候门只开了这么一点,那时候手艺真不行,魔鬼得从这个门缝里挤出来,大魔鬼就出不来,出来都是各种各样的、五色斑斓的小魔鬼。但当你后来变成专业的,门缝越开越大,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心里没有那么大的魔鬼。所以在创作中会经过一个很痛苦的阶段:门缝终于开了,魔鬼在哪里?手艺特好,坐在那儿没得可写,心里没有这个魔鬼。
我更多地拿诗歌做比喻,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很多人看到为什么一些人第一张唱片这么好,从第二张唱片开始就下去了。其实第一张唱片整个的手艺很粗糙,后来当你拥有所有专业的东西,自己也很专业之后,其实就是门开了,发现里面没鬼。这个就比较痛苦,还得去找魔鬼,心里这魔鬼在哪里?所以很多人后来就下来了,包括我自己。
当然如果你能够经历一些特别倒霉的时代,或者倒霉的东西,可能那个大魔鬼就破土而出。前天我在杭州开我的公益图书馆,麦家老师给我捧场。他说我发现一个问题, 1899 年生了一堆大作家,博尔赫斯,海明威,为什么?说正好一战的时候他们很年轻,那么年轻的心灵本来充满阳光,但大战中一千万死去,两千万伤残,重创心灵,魔鬼就长出来了。所以,找不着魔鬼别着急,它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来了。
高晓松
马尔克斯的《苦妓回忆录》,就像没牙的大魔鬼
我自己翻译过马尔克斯的最后一本小说,当时翻译成《昔年种柳》(又译为《苦妓回忆录》)。翻译这本小说的时候,如果不是我在坐牢,没事干,我根本看不下去。我就在那里,时间充沛得很,那么长时间,自己先慢慢做一支笔。因为那个里面没有笔,只发一个笔芯,我就拿那个稿纸,用早晨的粥涂在纸上,把那个笔芯卷成一根笔。也没桌子、椅子,就坐在大板上,拿着那根笔就想这个小说怎么写成这样。看了第三四遍,我才慢慢感觉到那是什么东西,就是对马尔克斯来说已经没有那扇门了,全是开的,但是那个大魔鬼,还能吞噬人的魔鬼,已经没有牙了。
《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不到 40 岁写的,那个时候感觉他心里的魔鬼是能吞食世界的,你看《百年孤独》就感觉自己被吞食了,到最后他 77 岁写的《昔年种柳》,门全开着,那里面趴着一个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牙也没有了,爪子也没有了的魔鬼,但是那只魔鬼心里充满了所有以前没有过的悲怆,可能还有一滴特别浑浊的、还带着眼屎的老泪。我看好多遍才明白一点,才动笔翻译。
我现在 48 岁,从十几岁开始写东西到现在,我还是能粗浅地感觉到整个痛苦的过程,“艺”和“术”什么时候能交叉出最好的能量密度,就是当那个门的缝隙正好的时候,那个魔鬼的力量正好的时候,他从这里出来的时候,那种幸福感是什么都不能替代的,而且也不能还原。每次人家问你怎么写出来的东西,你也不能还原当时那个门缝,以及你当时心里那个魔鬼,可能当时还很鲜活,五彩斑斓,你也没法恢复那个东西。
他们还说了什么
Q:你对于年轻作家有些什么样的期望?
阎连科:其实非常简单,对于年轻作家,今天他们要写作的任何才华都超出我们在座的,甚至超出上一代作家,但是有一点,什么是真的?这需要他们去辨别。就像许子东老师说的,我们处在一个充满巨大的谎言、或者说谎言也是巨大的真实的时代。哪个是真的?这是需要青年作者去认清去辨别的。
Q:你有没有觉得 90 年代以后出来的年轻人,什么都没有经历,能写出什么来?有没有为我们这一代感觉有点悲哀呢?
许子东:经历过那个时代以后,就比较不大能够说真心话,这是那个时代带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
我跟王安忆最近还谈这个事情,讲到文革的事情,王安忆的回答我觉得非常好。她说,不是我们要写,是没有办法。正好我们活在那个时候,我们长大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吃饭睡觉就是那个时候,那我们当然要写这一段。
其实文学创作还是面对一个人的人生,面对一个人自己的人格,面对做人最基本的东西。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不下于你的婚姻,你的爱情。所以,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魔鬼。你不要以为你就没有了,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有。
Q:90 后有一个巨大的目标,比如说买车买房之类,我们就会减少吃喝睡读的时间,甚至精力,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状,各位老师是否有解法?
金宇澄:我只能提一点建议,或者说 90 后、 80 后和我们这代人最不同的地方,他是家里的中心,而我们 50 后、 60 后,都是孩子很多,家长根本不管我们,我们反而要去注意家长的动向,家长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是巨大的差别。
当一个写作者你只关心自己,当然也有写出很好内容的作品,但是一般常规上,你应该要注意环境,注意长辈。文学都是一个回顾性的内容。读过这些,你才不会写出都是上下铺,大学里的故事,闺蜜的故事,它在舞台上有一层一层的背景。哪怕有那么一个奶奶或者祖父,或者什么人,三言两语,景深就不一样。
梁文道:在我看来,当整代人都想买车买房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厉害的集体经历。
Q:你认为在这个时代,作家的责任是什么?对现在这个时代又有什么特别担忧的事情吗?
金宇澄:因为每个作家的想法不一样,但作家的基本任务是把他眼中的世界写出来,把他感觉到的世界写出来,很简单的事情。至于作家的担忧,从我个人角度来想,我并不觉得文学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博尔赫斯这么说过,文学让人感动就可以。给你感动,给你消遣,等于《一千零一夜》的模式,各种故事。所以,作家可以很宏观地解释这个世界。但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应该把我熟悉的事情写出来,要把姿态放低,对世界的担忧也就是常人的担忧。
文内嘉宾图均由理想国提供,题图 Unsplash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关于文学和自己年轻时候的写作 阎连科 金宇澄 唐诺 许子东 高晓松都发表了意见”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