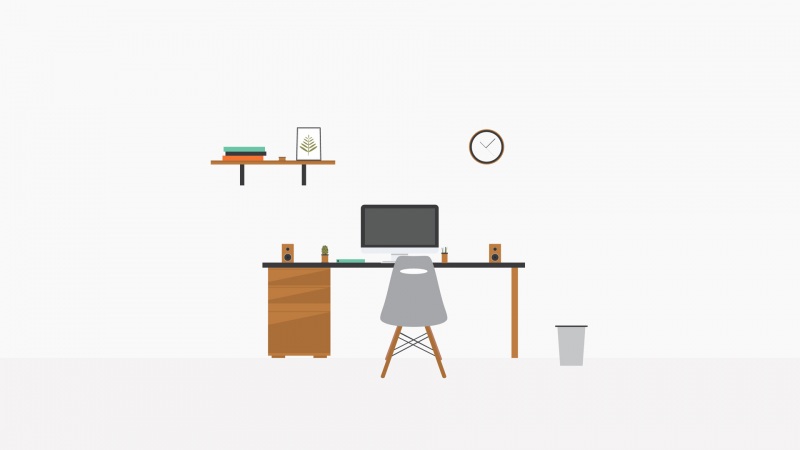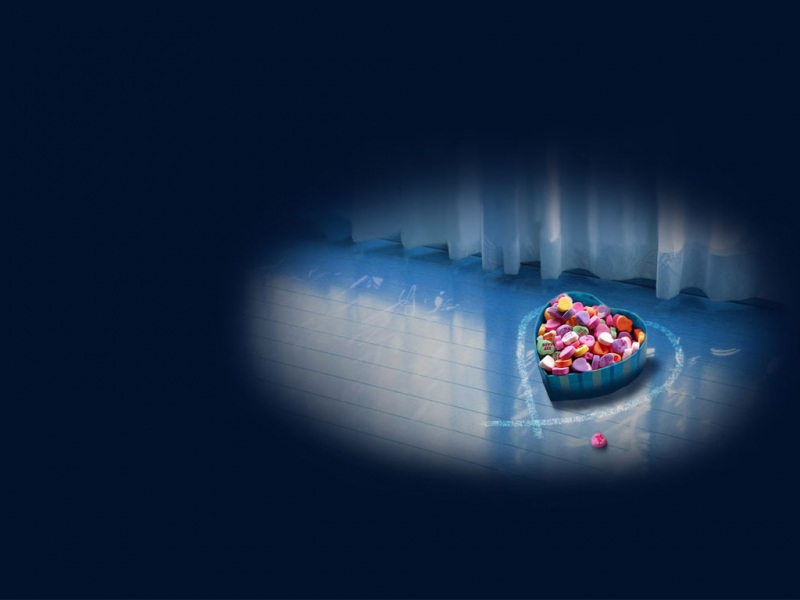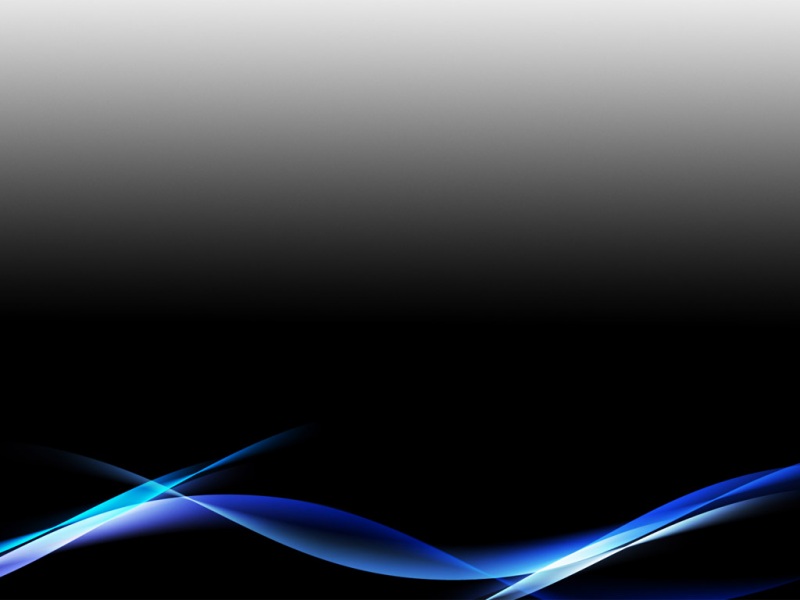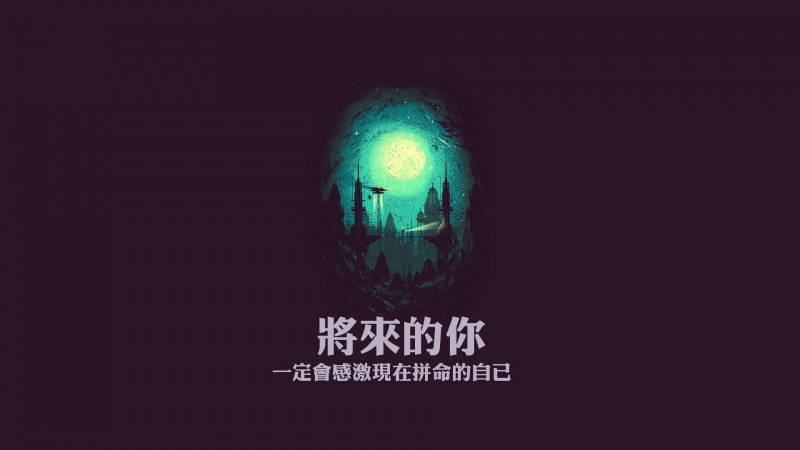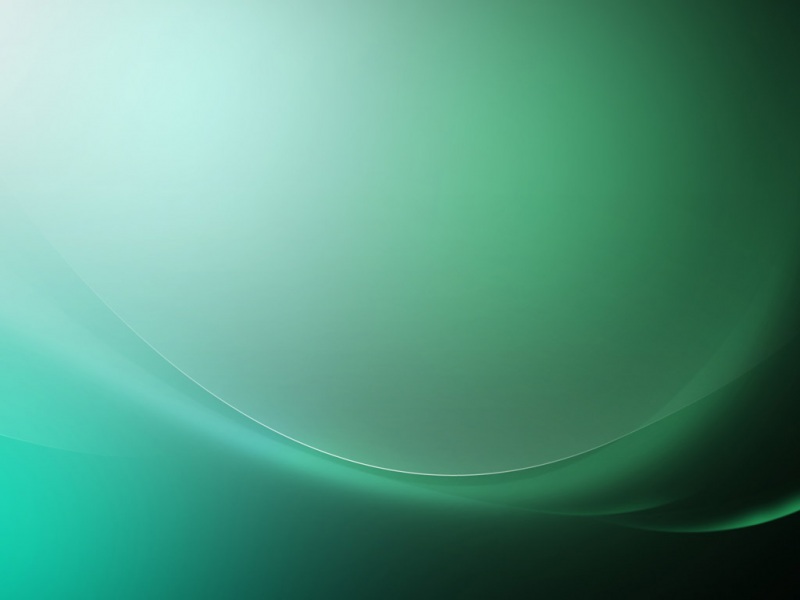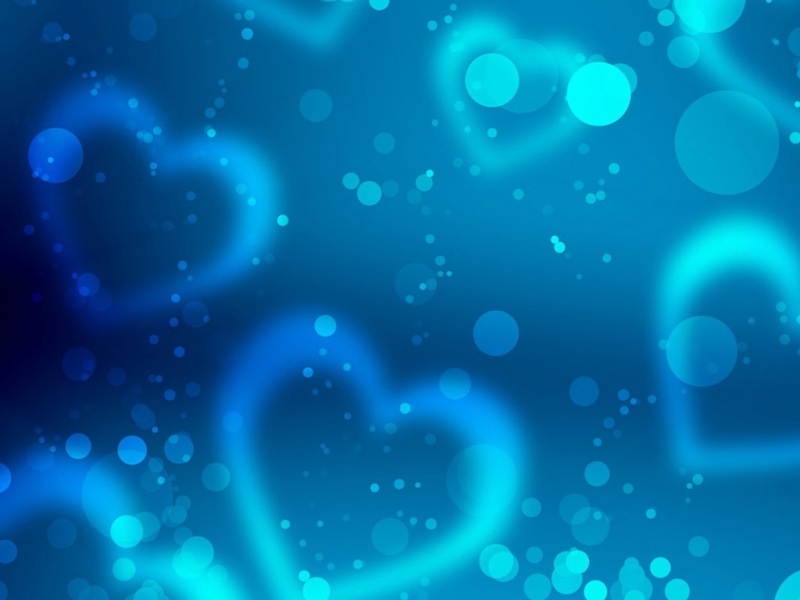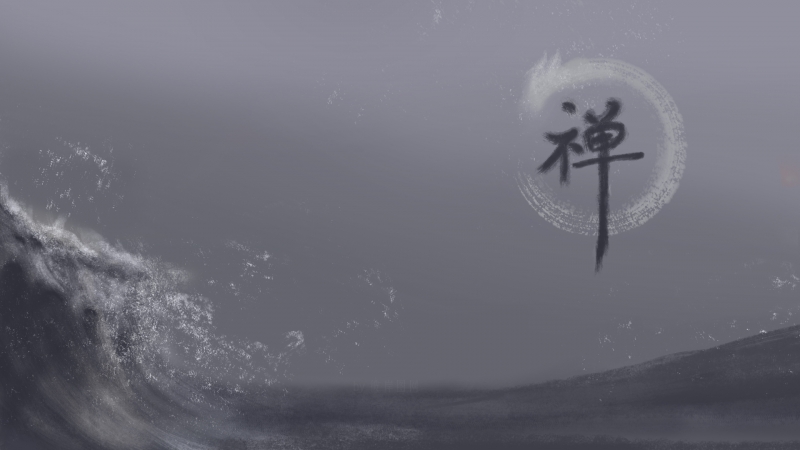提示:本文共有 14153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29 分钟。
图片来自网络,图文并无关系阅读须知:1, 不知该作是否有官方译文,这里仅为自娱自乐,不喜勿读;2, 这部小说是以中世纪为背景的,所以我会尽我所能为大家科普一些小说中出现的中世纪知识,若有与实际史实有出入,还望不吝赐教;同理,一些翻译上的疑问,也会尽我所能写出来,希望有路过的大神能不吝赐教;3, 书里有些语言和情节会出现脏话以及有颜色(你们懂的)的描写,好孩子不要学哦;4,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男主还在下一章,前面出现的都是男N,都是打酱油的!!!序章 御林苑(kingswood)老夫人死后的那个仲夏,我被带往皇家森林。我像个誓要苦修的人一样,自苦心智,跟头野兽似地生活在森林里,从这个夏至到下一个夏至。没有火种没有铁器,也不知肉的滋味。我像头森林里的猎物,狗教会我如何逃跑,兔子教会我如何在蕨草丛中藏身,鹿教会我如何挨饿。彼时,我莫约十五岁左右。身为弃儿,我自小便被送去了老夫人家,到了用得上的年纪时,老夫人让我做了她的使女。我在她身边就像她的左膀右臂,往往她还没开口吩咐,我便已动手办事。她极看重我;神血族里许多本家的闺女都未必有我这样的待遇,在平安嫁人离家之前,她们被视作是家里的负担,而不是宝贝。然而老夫人死后,她侄子和新婚妻子继承了领地,我便沦为一名普通下人,这个世界自有自己的法则,我身处其中,却无法为了适应它而磨平自己的棱角。悲恸与骄傲驱使自我放逐,隐入皇家森林。为了避开侍卫的搜寻,我不敢生火。饥寒交迫之时,我也几欲轻生。我从未思考过这样做到底会触犯还是取悦了神明。偶尔我也疑惑,是否是自己的顽固引起了掌管铸铁、熔炉及野火之神,阿多尔注意。有时又怀疑,我逃亡到御林苑到底是否真的出自本意?也许我早就落入火神的手掌心里,他要像通过击打考验盔甲一样,考验我的毅力。我也还不至于愚蠢到在盛夏里挨饿,只需拉下树枝,野生的李子便触手可及。我知晓每一颗可食用的植物的名字,我知道它喜欢长在哪一块土地,知道它什么时候可以丰收。老夫人和我骑着马到御林苑里给她的挂毯采集染料和用于食用以及疗伤的草药时,她把这些都教给了我。从根块到茎秆,从花朵到树叶,从种子到果实,她教我看懂神明是如何标识每颗植物的,这样我们便可知道它的质地,是性温良,还是性寒毒,又或是两者皆具。她教会了我唱许多草药的歌谣,以便我将所学的东西牢记在心:这些歌谣又像谜语,又似祷词。而老夫人的女执事,阿娜和库克教会我这些植物的其他用途和其土话的别名。青草药上,神血族一无所知的东西,我们这些草野庶民却了若指掌。自打逃进森林里以后,我便不再祈求神明的庇佑,因为他们早已漠视了我的祈祷。我全身心仰仗御林苑的施舍。但即便我想拒绝神明,我却无法躲避他们,因为他们无处不在。御林苑就像是神明的林苑,一切都有据可循,到处都硕果累累,赏心悦目。我采集不到的东西我便去偷:从田野里偷粮食,从果园里偷果实,从田鼠洞里偷豆子和种子,偷松鼠储藏的根茎。偶尔我会觉得,自己其实偷的其实就是森林本身,因为我可以在禁区里随心所欲地往来,别人埋头劳作我却可以悠然偷懒,这种兴奋之情让我飘飘然。我日复一日地游荡,从板岩河床的沟壑走到树木上苔藓密布的高山,哪怕在树木矮小佝偻的地方,我也从不迷路。就算是太阳被乌云遮盖,就算是身处峡谷底端的衫木树下,我也能辨认出太阳的方向,这是我的天赋。图片来自网络,图文并无关系尽管现在的我走得更远,知道这个世界是多么宽旷,但我依然觉得,身处御林苑其中,也许御林苑才是无边无际的。我们的村落宛如树林之海里的一座岛屿,是森林里众多岛屿之一,连绵的山脉上分布着农田耕地、草地原野、围墙篱笆和果园牧场。老夫人掌管着这个村子的同时还有塞斯国王以及她父亲恩赏的另外两个村落,她得到这个恩赐是因为她的佃地就在御林苑内并且受森林法保护。她编织的地毯受到国王的褒奖,并恩准她可以采集树林里的染料。从此她可以树林来去自如,而我跟在她身边,也自认为比庄园和农田里的下人更了解御林苑。村民获准可以在在集市路上走动,这些道路将树林里一个个村落如同穿针引线般连接在一起,有些则得到恩准可以去到丛林或是牧场、饲料场、矿坑等地方。当然,这都是要收费的,你总得给国王的守林员和护林员上缴点什么。据说,塞斯王极宝贵自己的东西,所以把森林里每头鹿、每颗树都记在帐本上;养猪的人发誓说,他们把猪赶到树林里,拴在橡树下养秋膘的时候,国王便连橡果也要按颗算他们的钱。奴仆只能砍伐榛树以及灌木丛里的枯枝,若是有人结婚,他便能砍到一颗橡木来盖房子。除此以外,他们都被护林员挡在森林外面。但我发现他们还是会偷溜进去:,被砍倒在地上的树木、剥下来的水果皮或是被陷阱绑住住的鹿。我一个偷猎者都没看到,他们太过狡猾,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要是被护林人发现,作为惩罚,他们会被挖掉一只眼睛、砍掉双手,然后丢去喂狼。在御林苑偷窃已经够糟糕的了,但陷阱更叫人厌恶。神明憎恶看到这些被遗落在地上的武器,标枪、弓箭、吊索,即便人和动物能够挺得过毒蛇的毒液,他们也可能丧命在这些人为陷阱上。村民们还有其他秘密,而这些秘密同样也被我发现了,那是由上古时期的榆树、梣木、或者橡树形成的巨大圆圈。树与树之间的枝干彼此紧紧缠绕交错,以至于树荫下没有可供树苗成长的空隙。我猜测这是片被遗弃的果树林。当我目睹果林深处那高耸的空间以及变成黑色的石头,我依然会感到寒毛直竖(解释:应该是古代人冶炼金属的地点,后被奉为圣域)。我小时候曾听过阿娜讲过这些地方的故事。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在我耳畔低声讲诉森林众神的故事,故事里有树木的守护神、果林的守护神还有石头和河流的守护神,我会被吓得不敢睡觉。老夫人则不信这些,所以我也只好不相信它们。许多代人以前,神血族人占领了这片土地,他们说,泥民信奉的神明,根本就是不是神,而是恶灵。他们下令禁止人们提及它们的名讳。下令禁止膜拜神明容易,但命令却无法抹杀记忆。有一天,我找到了森林里最古老的树,那是一颗黑色的橡树,树干大得连十二个男人手拉手也无法环抱。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阿娜曾将这颗树称为森林之心。我看到了用树枝和树皮做的布偶被垂挂在枝干上,右上边的布偶是为了治疗不孕,下面的则想召来流产,泥民女人深知要是被不定时巡逻的侍卫发现了她们,被悬挂在树上的就可能是她们自己,但她们依然大胆地将这些布偶它们挂在这里。图片来自网络,图文并无关系我并不是御林苑里唯一的居民,不管有没有获得国王的准许,森林还是居住着别的人。除了护林人之外,还有伐木工、烧炭工、矿工、打造盔甲的工人以及牲畜贩子,这些人皆为国王以及国家而奔波。我远远地躲着他们,远离他们的视线和他们烟熏火燎后的臭味。森林里也住着野人和游魂,至少阿娜是这么讲的,所以有时候夜里狐狸卡着嗓子的尖叫声,在我听来就像有鬼魂在出没,我便会相信她的话。我本该恐惧,但我只是提高警惕而已。我觉得自己并不危险,仿佛我本人也是游魂,可以来无影去无踪。夏末时分,我穿过瘠妇峰(barren woman peak,barren woman 无法生育的妇女)与秃头丘之间的山道,沿着山脊一路向南,上山下山,下山上山,一直走到一座不知其名的大山和一片森林中,这片森林已经被修剪过,就算有人策马飞奔而过,也不需要低头避开头顶的树枝。这个地方古木森立,粗壮的树干顶起浓密的树荫,脚下是稀疏的青草,我看见一头红色的牡鹿往来于绿草丛中的灰色树桩之间,正在啃食青草。它戴着顶由十三只牙齿和破烂的天鹅绒做成的王冠。他抬起头来,鼻子喷出气息,接着我便听到了猎人们的低沉的马蹄声、噪音以及马勒的叮当声。我赶紧拍拍手提醒那头鹿,然后我们一起跑掉了,他跑一个方向,我跑另一个方向。猎狗知道牡鹿的气味,紧追而去,悄然跟在猎狗旁边的是训狗人,领头猎人则用号角发出追捕的信号。我跑到下风处直到心脏砰砰跳的声音盖过了号角声。我在一条碎石密布的河流里艰辛地走着,一路摸索走到一堆被冲上岸的马尾草里。我躺在那里,被一群蠓虫包围着,不住地喘气,汗流浃背,抖如筛糠。当号角声和猎狗的声音再度响起,并且慢慢靠近时,我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我看到那头牡鹿跃溪而过,蹦到对面岸上,溪水溅上了他的腹部,他的呼吸声粗粝,仿佛是人的咳嗽声。猎狗们把他赶上岸,咬住他将之扯倒,猎狗纤细的身体时而拉直时而扭动,撕咬牡鹿的胸膛和腹部。牡鹿的身体彻底倒下,领头猎人见状将一根鹿角插进地里,匕首伸向牡鹿裸露的喉咙。我像故事里那只躲在草丛里一动不动的兔子,自欺欺人地以为那个手持棍子的男孩看不到自己。我明白兔子其实并没那么愚蠢,它只害怕得无法动弹,腿迈不开了,眼睛眨不了,只能呼哧呼哧地呼吸,眼睁睁听凭鲜血喷涌而出,洒满全身。猎人们将用杯子盛满牡鹿的血做了次献祭,接着挨个喝杯子里的血,喝得满口血红。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从他们的咆哮声里辨别出一两句话来,发现他们说的是神血族的雅语。但我并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于是我静默不动。穿着一身脏臭皮革衣的猎头抓住鹿角,高举到头顶的位置,然后昂首阔步地来回走来走去。其他人哈哈大笑。但这并不是在嘲笑什么,他们在召唤狩猎之神普雷的阳之化身,鹿头人身的猎人。我发誓躺在那里的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喷在了我的脸颊上。牡鹿身体支离破碎:被掏出内脏,被剥皮,被大卸八块。马儿们安静地站在一边,它们训练有素,已不惧血味,狗们则吃起和着血肠内脏的面包。他们离开后,岸上血迹斑斑,我脑里浮现出一块火烤得发黑的腰子,我垂延那肉的滋味,直到肚子发疼。图片来自网络,图文并无关系那场狩猎让我学会了日夜提心吊胆。我往更高更荒无人烟的地方走,去到野兽出没的地方,那里有熊、猞猁、狼和野猪。我研习它们的习性,避开它们的地盘。它们很可怕,但国王的侍卫和他的猎狗更可怕。我给自己找了一处兽穴,是位于秃头丘山顶的一块裂开的岩石缝。只有雄鹰才能飞到这个乱石密布的高处来,它们并不会理睬我。我搭起一块平坦的岩石作为裂缝的屋顶,在洞穴里铺满叶子,周围撒上树枝用来吓退不速之客。从这个位于高处的小巢里,我可以看到下面的山谷和远处的村落,看到一个泥民住的的大杂院紧挨着一座庄园的石墙。河流蜿蜒地流经村落,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偶尔在艳阳下银波潋滟,偶尔污泥堆积变成褐色。我看到两个贱农和一头驴在漩涡状的田野里犁田,留下一条条犁沟,好待来春播种。三种色彩形成圆圈,一个套着另一个:深棕色的是从犁沟里翻出来的泥土;金色的是夏麦收成后留下的残茬;绿得发光发亮的是冬麦。老鹰在我下方盘旋,寻觅为搜集谷子而不小心暴露了自己老鼠。神明所造的这个世界过于辽阔,衬得我们愈发渺小。我们兜兜转转,每走一条路便如抽出一根细线,直到细线相互缠结。我身处其外,可以看到这些村民们给自己的世界结结实实地打上了节。我心想,要是我小小足迹能够取悦御林苑,我与村民不也没有两样?从森林的迹象中我看出,严冬将至。冬青树刚结满厚厚的果实,鸟儿随即便啄食了个干干净净。乌鸦在收割后的田野里争吵鼓噪,深山里猫头鹰叫声便像像守丧的寡妇在哭泣。动物身上的毛发长得更粗厚了,苔藓生得更密集了。北风裹夹冰冷的雨水穿过树林的斜径,大雪随之而至。来御林苑时我身上带着两件衣物,一件是我穿在身上的衣裙,还有一件阿娜给我做的羊皮斗篷,斗篷上染画着护身符,以免受恶风伤害。这件斗篷同时也保住了我的命,但它无法驱离寒冬。年迈的老媪(the old crone)爬进我的斗篷里,伸出冰寒的双臂抱住睡梦中的我。我本以为,我未雨绸缪,在丰收的月份里勤勤勉勉地风干果实,储藏坚果和种子,便能抵御寒冬。但其实根本远远不够。我饥肠辘辘,肋骨下空空如也的腹部仿佛变成了个空洞,寒冷在那里扎根。麋鹿们在地里刨雪,寻觅丝丝绿意。而别无他法的我只能瑟瑟发抖。在储备的粮食都吃尽后,饥饿逼迫我从洞穴里出来,我前往连老夫人也从未去过的森林的深处,去吃长在那里的不知名的植物。我吞咽冻僵的根茎,啃咬树上的嫩枝和树干里面柔软的树皮。我吃木耳,吃青苔,吃蛀虫啃噬后变成粉末的木头。毒药有百形千面,并非所有毒药都是入口苦涩或是恶臭难闻的。毫无疑问,神明给予的启示都是真实的,只不过我们的解读却常出现差错。我发现我不能只依赖老夫人教给我的东西。辨识新的植物时,我会先闻一闻,然后放在舌头上尝一尝。我总能辨认出厨娘库克下在煮锅的草药是什么。吃一堑长一智,我也常会呕吐,有时会发热,要是难受得太厉害,我就吃点陶土来缓解毒性。我不再按时来月潮,我开始担忧自己是否还活着,还怕自己时候未到,便成了一个不会生育的枯槁老人,受了伤后会痊愈得很慢,牙龈里的牙齿会松动,我在老夫人弥留之时,在她身上看到过这些使人日益消损的疾病。饥饿引发的阵痛,与分娩的疼痛相似,痛感会愈来愈迟钝。这是件好事。我的眼前浮现出清晰锐利的景象:四五只红色的麋鹿在浅黄的晨光下在白雪覆盖的山地上蹦跳。它们并没有相互追逐,而是奔跑着,也许只是因为为了玩乐。黝黑的树木,白色的雪地,鹿的蓝紫色的影子在雪地上拉得长长的。图片来自网络,图文并无关系冬日昼短夜长。我嫉妒熊可以在地下长眠,靠梦里的水鱼和浆果为生,我也嫉妒那些安稳地睡自己的床上和自己屋里的人,我曾也是他们的一员。我嫉妒每个有灯火蜡烛壁炉为伴的人,我躺着,久久无法入睡。有时侯黑暗倏忽而至,转瞬而离,有时候,也是最难熬的时候,黑夜包裹了我,我在着覆盖了一切的黑夜里独自清醒着。当睡着时,我众人一样,会沉入神明沉眠的汪洋国度。有时沉眠会为我疗伤,让我的悲伤随波而逝,然而我在沉睡时,却会屡屡遭遇噩梦,不得不逃回清醒的世界。沉眠是神明猞猁的化身,因而性格狡诈多变。最后我学会了在沉眠的阴影里漂浮,那是处于将醒未醒的状态,我可以抓住柔滑的梦境,就像一个孩子将滑溜溜的鱼抓进网里。我也学会了如何将它们紧握不放,因为梦境千变万化,一旦从你的手机溜走,便会变得凶神恶煞。老夫人曾来过这些梦境,给我带来羊腿面包和一只枯萎的苹果。她和我一起吃这些食物,但在生前她从未这样做过。我的梦恍如真实,一只釉碗里装满了奶油,一束光下,有只绿头苍蝇在嗡嗡地叫。她让我去查看酒桶有没有漏,去采些薇拉维克(willawick实在不知是啥,只好音译= =)预备做黄色的染料,还有那么那么多还没做的事情要做。我生怕不能常常在梦里见到老夫人,故去的人理应无牵无挂,心无妨碍,因此在他们逝去一年以后,我们不可以提及他们的姓名。神父说,他们的游魂很可能会因此而流连倾听,然后迷失在黄泉路上。也许梦境也有相同的力量,梦中的话语也可以让灵魂来到你身边,当我在梦中恳请老夫人多呆一会儿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就近在咫尺。但一旦醒来,我感到的只有更为深切的渴望和孤独。在最为漫长的冬至夜,月黑之夜,我做了一个真实之梦。这样的梦,有些可以预示未来,但我的梦却告知了我的过去。梦境的气味挟持了我,但我依然知道它是真实的,因为在普通的梦境里,我不会闻到这样的气味。这个味道,我从未在任何脚下的草药上闻到过。这种从岩石之间升腾而起的灰尘的芳香,仿若烤炉上的面包味。但我识得它:这是大山的味道,却不是御林苑里山脉的味道。在梦中,我跟随着父亲走上夹在两座高峰之间,布满白雪的陡道。那里山峦嶙峋,寸草不生。年纪尚小的我骑着一匹小矮马,而父亲则坐在高大的红棕色的大马上,领着一匹拖着行李的毛驴,心情愉快地唱着小调哄我。那是一条一边靠墙的铺着鹅卵石的小道,我们沿着它走到路的尽头时,他在马上转过头来,红色胡须之间的嘴巴一裂,冲着我笑。我的小矮马打了下颤,我畏缩了一下,感觉到马儿可能爬不完这最后几步。其实马儿比我更心急,她知道在道路的另一边,家就在路的那边。云雾缭绕在我们周围,而云朵的下方,云朵的阴影在山谷中狭长的湖面上移动,我们的村子就在沿湖畔而建的村落之间。湖水比天空还要湛蓝,阳光下湖面水光滟潋。然后我父亲回头看我,大声疾呼,然而我却一句也听不懂,也许那是一门我只能在梦里才听得懂的语言,但我知道他是在表达,我们陷入了危险中,因为他指着我身后的一排骑着马的男人,他们就在另一座山的山顶上。他们甲胄泛光,黑旗飘扬。他们的马蹄扬起灰尘,正冲着我们奔来。当我醒来后,内心被父亲的影像深深震撼,让我几乎没有去思考为何会有士兵出现在梦里。神血族人自认为自己是神明的后裔,但是我们泥民却不然,一个男人的妻子如果生下了和自己长相相似的孩子,那便说明他的妻子对他是忠诚不渝的,这样的男人在我们眼中,便是幸运的——而在梦中,我意识到我的身上有父亲的影子。和下人们在一起,是没爹的杂种也没什么可耻的。但,我还是想知道我父亲是谁。我并不觉得自己缺乏母爱。还很小的时候起,我便把阿娜当成了自己亲生母亲。后来我又猜,我会不会是她和某个身份卑贱的园丁或是马夫生的杂种。但她不止一次告诉我,我是个弃儿。到了会跑跑跳跳的年纪,我被送到了老夫人家。她们数了数我的牙齿,估摸我应该是四岁左右。我即不会讲贵族的雅言,也不懂庶民的土话,所以我开口讲的话没有一个听得懂。她们起名“福气(LUCK)”,因为我的头发红得像新铸的铜铁,而红头发的人都是受到机遇之神(Chance)眷顾的人。村里头还从未有人有跟我一样的头发。她们对我不记得庄园之前发生的事情并不惊讶。我们会梦见自己还是婴儿时的事情,但醒来开始干活时,又忘了梦里的事。她们给我派都是简单的活儿:拖地、洗碗、给地毯梳穗,倒泔水、粪尿。我总是干到一半便自顾自跑掉,做起事来三心二意。于是阿娜便找来一根柳条打我,打完了后她又会安抚我,说我是她的小福气。这便是我的童年,直到有一天老夫人把我带到她身边。那时的我,以为庄园和村子便是全世界,我们是这世上唯一居民。回忆这东西,像个臭脾气、不听话的仆人,你要找它时,它偏跑得不见了踪影,你要它走开时,它偏要一脸狂傲无礼。也许那便是它总在为何我变得虚弱时,不断涌上脑海的原因,回忆里最折磨我的是,老夫人连续五周高烧不退后的样子,她躺在床上,被子掀着,高烧让她肉都瘦尽了,只剩下一层皮晾着骨头。她甚至承受不住床单的重量,哪怕那时用上好的亚麻纺织而成的。她的手指像扯着看不见的绳子,不断做出拉扯、打结的动作,空手在脸上拉扯着,仿佛感觉寿衣已经盖在了自己身上。有一次,我拿来一盆水给她擦拭身体,老夫人撑着胳膊支起身子,说:“我侄子跟我保证过,他掌管这座庄园的时候,他不会硬要你留下来。他说他会让你做他妻子的女仆,只要你合她的心意。但如果她不中意你——那么,你随时可以离开。这是我能为你争取的最好的结果了……”她躺回床上,我用冷水沾湿毛巾,擦拭她的手臂和胸脯。即便只是说这么几句话,也已令她喘息不已。“你要是把他们都服侍好了,那当然最好不过,”她微弱地笑道,“你得努力管好自己嘴巴,我知道你总时不时要心直口快,说话没个顾忌。”我冲她笑了笑,尽管我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被允许离开庄园说不上是个恩赐,这里每堵墙、每块石头,哪怕就是炮台上长的杂草,对我来说都珍贵无比。我也是一颗杂草,紧紧依附着自己熟悉的地方。老夫人去世后,我对自己应该做什么并未多做设想。那时,她缠绵病榻,去得并不轻松。她教给我许多疗方,但都没有凑效。她从不呻吟哭叫,直到最后一天,她控制不住自己了,已经一脚迈到了黄泉路上。最后,我给她喝了“走好汤”,那汤药只能减轻她的痛苦,却无法治病。葬礼后我们只给她做了七昼夜的法事,因为要在她侄子来之前打点好庄园。祭司做好老夫人的陶土面具,送到部落的神庙里和其他亡者的面具摆在一起。我们相信,遗物会呼唤死者:她织布的梭子和线筒、梳子和贝壳发夹、盘子和杯子、琥珀刀柄的匕首、她系在铁链上的小剪刀、内衬裙、鞋子和帽子。我们让这些遗物随她一起火化,看着白烟升起,祭司把她的烧剩白骨放在地上,将骨灰撒向溪流,然后犁了烧焦的土地。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情,让她灵魂升天。然后我们要小心翼翼不直呼她的名字,我们称她“老夫人”,我现在也依然这么称呼她。在御林苑的冬日里,我觉得自己比她更悲惨,我哭喊着责怪她把我养成了个除了一身傲气之外一无所有的人,而傲气是最要不得的东西。要是她没注意到我该多好,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杂草丛生花园里一个灌木丛后面给蚂蚁造宫殿,她跪在我身边,指着一只拖着一片叶子的蚂蚁,说:“瞧,因为小菊花很香,它们就把花朵儿当作是自己的巢。我们把花朵碾碎揉进面团里给生病的人吃,那香味是有疗效的。”要是我没有学得快,又急切地追问她,那该多好。那样我就不会这样骄傲,以为自己也是个身上流着神血的贵族,仿佛跟别的泥民(mudfolk,书中的骑士阶级对老百姓的贱称。)不同,不是出自污泥和浊痰。我本可以忍受自己的新老爷新夫人,像其他仆人那样,忍受他们的怒火,容忍他们的牢骚和刁难,逆来顺受。老夫人死后,阿娜就不再管钥匙了,他们说她太老了,这样的重任会压弯她的脊椎的。当钥匙交到我手上时,以及那随之而来的责任,我诧异地发现老夫人原来管理这样一些用绳子联系起来的大小事务,将它们处理得井井有条。我内心交织着喜悦和担忧,忙得连抱怨的时间都没有。我给新老爷罗列预备事宜的清单。我会认字,会写神符也知道怎么记账;老夫人从不认为一个下人会读书比猪会飞还古怪,也不认为没必要学会识字断文。在她的织房里,我发现了一张她下一张挂毯的设计图案卷轴,就锁在橱柜里。纺车已经上好了纱线,但她还没开始织就生病了。她画的是一名少女站在草地上,周围繁花似锦,但那些花朵绣得并不合情理。霜麦应该是晚冬开的花,却在开在盛夏的太阳花旁边,而园林里的紫罗兰和深灌丛里的天龙巾(dragon’s hood不只是啥,只好直译= =)纠缠子在一块儿。纱线就固定在草图上,她为少女披散的头发,选择了紫红色的羊毛线,那是用甲壳虫的翅膀碾碎制成的非常罕见的染料染成的(早期的紫红色,用的是蜗牛的壳,而甲壳虫制成的应该是深红色carmine,疑为作者有误。)。我烧了图画,把羊毛线留下作为念想。我把它一起带去了御林苑,缝在自己的外套上。她的侄子和侄媳到的时候是春天,随行着一群兄弟和堂亲,亲朋好友和照顾起居的仆人。庄园里唯一个出自“神血族”的只有老祭司,于是他到大门前迎接他们,将他们领进外院。那里有颗神木,那是一颗红叶李树,粉红色的花朵纷纷落下,落在他们天鹅绒衣服和毛衣还有闪闪发光的马革上。新郎头戴着嫩枝做的王冠,上面的叶子嫩绿鲜黄,而新娘的王冠里则编入了鲜花。那一晚我在餐桌前伺候。新老爷和新夫人在上座上公用一个餐盘。新老爷帕瓦大人,全名叫帕瓦 达摩 卡培拉,来自库拉克斯族的阿尔席恩一家,年纪尚轻,面白少须。他的新娘,莱拉夫人,来自库拉克斯族的欧菲瑞斯一家,她的脸又白又胖,就像揉捏得当的白面包。她年纪比我还小,还不到十三岁。之后,客人们喝得满脸红光,他们说的笑话也越来越粗鄙,肉骨头啃得干干净净,酒撒了一身,最后一轮高歌和敬酒结束之后,新婚夫妻被送到了老夫人主卧的床上,床前悬挂着老夫人最漂亮的挂毯。我们这些下人则在昏暗的牛油灯下熬夜工作,督事要我们不停的把储藏室里的东西搬来搬去。当我看到他站在角落里撒尿时,我毫不诧异,把他当作是条靠撒尿画地盘的狗。我们把大厅的下人睡的板床房让给了客人,自己去睡外院。那夜我无法入眠,当太阳升到墙上时,我听见鸽子在咕咕地唱歌,仿佛在说: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去查了一下鸽子的叫声,大概是这样的“姑古鼓故~”咋听之下,确实有点what will you do的感觉)当天早晨,我伺候莱拉夫人梳洗的时候,当我解开她裙子的拉带,她瑟缩了一下,于是我问她,是不是觉得疼?我知道有种药膏能够纾缓擦疼。她身量未足,臀部扁平,乳房还小,她还是个一个孩子的身材,脸颊、手腕、膝盖和腹部,一个孩子该有肉的地方她都胖嘟嘟的,但她却承受了一个男人的体重,我猜对她来说他太重了。她甩了我一巴掌,告诉我没有她的允许不准饶舌。从此,我懂得伺候她时得沉默。慢慢地我越来越了解她,知道她是用了什么花招让自己面白唇红,我为她端屎端尿,洗她的月事带,但她从来不正眼看我一下。我常祈祷自己在督事面前是个透明人。从我把钥匙交给他那天起,他便开始总挑我的刺,我打理庄园的方法不对,我管理佃地的方法也有错。他是部落贵族的远亲,帕瓦爵士的父亲派他过来监督这里。他常借故抽打我,说我态度狂傲,令人生厌。若是我直视他的眼睛,或者直呼其名,他立马把我揍得脸青鼻肿,当我伺候他们用餐时,得强颜欢笑,不然也是一顿好打。尽责工作带来的自豪已经烟消云散。不只我一个人发现,工作变得拖沓缓慢,本来一个小时能干完的活要拖上一整天。织布机上的纺线必须有条不紊。阿娜说,“臭鸡蛋孵不出小鸡。”下人们开始偷偷在幽暗的角落里谈论主子们脸上的“天气”:督事“乌云密布”,莱拉夫人“大发雷霆”,帕瓦大人“阴沉不语”,憎恨成了我们的粮食。平日里,他们把阿娜当作是个拖后腿德,却又让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干她做不了的活。我有充足的理由离开,但又有那家领主愿意收留一个敢自己找下家的贱仆?我在这个家里过得十分压抑,河边的枢轴草抽出嫩芽,姬吻花开得正妍,我错过了采撷种子时间,甚至无法享受到被刺扎疼手掌痛感。与此同时,我学会了为出门而扯谎,晓得在督事面前说一套,跟莱拉夫人说另一套;我学会厚颜无耻地撒谎,玩忽职守,一切下人欺上瞒下、隐瞒事实的方法我都学会了。起初,我求助于神明们,以为他们能听到我祷告,我求得最频繁的是纺织之神 文德。我在神台上供奉了几梭彩色羊毛线,一座小小的神像就安放在老夫人织房的神龛上——尽管老夫人是库拉克斯神族的后裔,但纺织之神也青睐她。我祈祷神明告知我的归属,让我融入世人之间,使我无惧无忧。羊毛烧焦的气味使我想到不是神明,而是老夫人,我没有获得安宁,我的心变得日益冷硬,心房却胀痛不已。如今我明白了,文德,这位纺织之神,其实早对我的祈求做出了回答——她右手拿着梭子,但左手却举起剪刀。然而让我万万没料到的是,帕瓦大人居然夜深到我睡的木板床上来。那时他妻子刚上了他的床才不过两个月。他从父亲家里带过来了一个泥民出身的女人,尽管她已经怀胎五个月,不需要干活,但她的待遇与我们差也不了多少。他把她关在与庄园连墙的一个泥土屋里,一个跟猪棚似的地方,兴致来了他就去找她,莱拉夫人气得乱扔东西、呼天抢地,他也不理不踩。我以为帕瓦大人一定在她俩之间忙得不可开交,但我又怎会知道男人就是贪得无厌的东西?老夫人周围的大多数仆人和她年岁相仿,都是上了年纪的女人,而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服侍她的男人要么是老叟要么是稚童,有的是老祭祀,有的是厨房里的小帮佣。后来帕瓦大人来了,带着他的督事、侍卫、仆从、养狗人、守林人、园丁以及一个专拍他马屁的马倌。入夜的大厅里,有资格睡上一觉的下人们挤睡在厚木板上,幸好有被褥发出羊齿蕨甜丝丝的味道,才掩盖了他们身上扑鼻而来的体臭。我睡在主人的床屉里(中世纪寝具设计的特点——主人睡的大床下面安装有床屉,床屉是木板,铺上稻草之类制成的床褥后,便可供仆人睡,也可以用来放东西),方便为莉拉夫人端水倒酒、清夜壶或者打死一只在她头上嗡嗡叫的苍蝇。我把这段故事讲得啰里吧嗦的,再怎么说,这段故事又有什么好讲的呢?事情是,有一晚帕瓦大人到了我睡得木板上来了,我推开他,告诉他,我来潮了。女人的血——尤其是从她子宫里流出来的不洁之血——会让男人害病。只有处女的破处时流的血才能给男人壮阳,并且还能治疗阴茎溃烂。他离开了,但我知道他还会再来。我叫醒就睡在我身边的阿娜,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下次他再来我该怎么办,阿娜?”我焦急得不知不觉提高的声量。“嘘,”阿娜说,“要是帕瓦大人喜欢你,那这是件好事。这样你就不用受督事和莱拉夫人欺负了。”我要听得不是这样的建议,我说:“我不用他喜欢我,我谁也不喜欢。”“你下体是死的吗?”她问我,“那倒是叫人可惜。你已经十五岁了,却还是个姑娘!你应该嫁人生子了;而不是像小时那样以为自己还能躲在老夫人的裙底下。如果你不能取悦帕瓦大人,你就会被送给他的侍从们玩弄。你最好想想怎样才能留住他,而不是把他撵走。”听到这话我开始哭了起来,阿娜走过来躺在我身边,抚摸我的头发。“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小福气,”她在我耳边低语,“我知道一、两样老夫人没有告诉你的东西,能帮把帕瓦大人的心拴在你身上(keep sire pava tied to your thumb)。我们找点‘烈烛’(后文可以知道,帕瓦大人的毛病并不是性欲不强,而是早遗早泄,这种叫做“烈烛”的东西,既可以做壮阳药,又可以当食材,而且见效快,估计更像春药。我本着考据的心理查了一下,结果查出来好多种= =,实在不知道‘烈烛’此物,是哪一种,但换个角度思考一下,蜡烛形状的,那可能就是某种动物的鞭了吧)让库克放进他的菜里——不过你得自己亲手给他端过去。这能让他坚挺上半个时辰,然后他就会觉得这都是因为你让他欲罢不能,比他妻子强多了。你有没有听他们在晚上偷偷说的话?帕瓦射得比条狗还快。难怪莱拉成天气急败坏的。”我气阿娜,气她给我出这种主意,赌气不跟她说话,好像是她害我被帕瓦大人给盯上的。库克的建议稍微好点;她说潮湿的灯芯能让他那玩意儿变得软绵无力,并告诉哪里可以找得到,她一声不吭地看着我把它加进帕瓦大人的菜里。我还找来一些“绝子”白果,这是山里的女人用来避孕用的草药。如果这样不行,就用另一个办法。我把双腿之间的耻毛打成结,挡住子宫的入口。我好几晚都瞪着眼睛不睡,但他却没再来到我的床上来。直到那一天我在山涧采蕨菜,他骑着马追着我跑,我跑得摔倒在地上。他说他追我,就跟追猎一只狐狸一样有趣。我本打算如果无路可逃了那我就屈服,但当真到了这一刻,我却急忙往爬下河岸,去拿石头,但我还没拿到手,他便抓住了我的裙子。我像只野猫一样对他又抓又咬,弄得他一身咬痕和抓痕。很快他便射了。他一站起身我便把裙子拉下去。我一身大汗,脸上涕泪肆流。他低头看看自己的阳物,把它塞进自己的裤裆里。穿好紧身裤,系紧衣带。“怎么没有血?”他说,“你把我给骗了。你没有束发,伪装成处女。是不是哪个马童给你破处的?”我甩手给了他一巴掌,挖苦道:“大人,一个马童都比你强。就想你妻子说的:你在马鞍上根本呆不久。”莉拉夫人并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只是想挑拨他们,报复他毒害了我。我看得出我的嘲讽击中了他的要害,但他笑容不变,说:“下次我们再见面我会慢慢来的。我会戴上我马刺,让你不会再乱吠乱咬。”那一刻我哭得说不出话,我在心里想过很多次,要是这件事发生了,我能做到什么?我做不到什么?我为此噩梦频频;但现实不是梦,过去无法被挽回。他骑上马之后,丢了我一块围巾——他用来绑在马鞍上的一块破布——说,“我给你带了条头巾。戴上,别哭了。既然你都把身体给我就别再哭哭啼啼的了。我这辈子还没见过那个女人嚎得跟你一样大声。”我走进河流,坐在水里洗掉身上的污泥和那些白色的精液。然后我发现他说得没错,我没有流血,尽管我之前从没和男人睡过。我在阴道打得发结起了处女膜的作用,阻止了他的浅插。毛发拉扯出来的地方肿胀酸痛。我颤抖着手用头巾把头发裹住,然后走下山。看到这一幕,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尽管帕瓦大人夸下了海口,但他再没来骚扰过我。我猜他应该更喜欢心甘情愿的女人。而阿娜说得对:要是我取悦了他也许事情会好过一点。我要承受莱拉夫人的唾弃,忍受她把我的手臂掐出半月形的伤痕,忍受被帕瓦大人的侍从的嘲笑和动手动脚,因为我从此被他扔到一边去了,督事偷偷说我的坏话,我和阿娜的关系也变得僵冷,因为我们都不再互相理解——文德的织女神,将我维系我的线一根接一根的,剪断。在这里,早春是最贫瘠的时节:粮仓里的粮食和尘土参半,火腿被刮得只剩下骨头,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甘蓝和芜青。御林苑里,麋鹿吃光了树枝的嫩芽,当中虚弱不堪的那些,则成为狼群的食物,或是倒在地上就此腐烂,直到溪谷的华木冒出红红的枝丫,河边的柳树摆动绿莹莹的柳枝,蕨菜舒展了叶子,嫩芽从枯叶中喷薄而出。我内心的悲伤也舒卷而出,过往一直伴随着我的痛苦化作浅淡的哀伤。我思念老夫人,不仅仅因为她的养育之恩,而更因为她这个人。我回忆她的面庞,夏天,她要是不把那条浆成蓝色的头巾戴上,她就会把脸晒得棕黄,到了晚上我给她梳头发,我就会调侃她只剩额头是白色的。她右边的脸颊有一小块青色的纹身,那是她的部落的图腾,库拉克斯;而右边则纹着里尼克斯的神示。里尼克斯是她丈夫部落。在我来庄园前,他便死于一次国王发起战争,阿娜说他的亲属把老夫人送回了娘家,指责她不会生育。他父亲把她安置在最寒碜的庄园里,给她的钱仅够度日,等着把她嫁给别人。然而她没有再嫁,“我可不会遭两次罪。”她仅仅这样对我说,别无他辞。她生气的时候眉头会出现两条细纹,比起阿娜的柳条我更怕见到她露出这样的表情。我要是在干活的时候心不在焉,或者和其他下人闹腾得太厉害时老夫人便会对我露出这个表情,我常害怕她的鬼魂会对我生气,因为迄今为止我是如此忘恩负义。这是我与生俱来的傲气使然,没有人强迫我。她并不亏欠我什么,而她依然对我倾囊相授。她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看到世间的美丽,看到四季中一切知名的以及未知的色彩。我爱她所爱,如此顺理成章。我逐渐不思饮食,身心俱惫:天寒地冻时我不奢望有得取暖,浑身湿透时我不奢求可以烘干。我屈服于天气和本能,学会了忍耐——或者说是淡漠。但是饥饿驱使我横穿森林,我搜寻可以果腹的植物,但它们都还未到时候。就这样我来到了火棘树下,这片树林只有这么一棵树。它独自树立在一片空地上,周围是横倒的橡木,树下长满了名为“来压我”的蓝色小花。在灰色的棘树冠上,太阳神点燃了通透的橘红色的浆果。树枝长出银色的枝丫,嫩叶随风而动。这棵树是献给艾多神的:枝干如铁般硬朗而果实如火般殷红。老夫人告诫我千万不能去碰那些浆果,就连鸟儿都不敢靠近它。我曾有几次从这里经过,冬天并没有令它枯萎,那些果实看上去红润饱满。而我饥肠辘辘,饿得只剩半条命。我摘了一颗果子放进嘴里,咬开果皮,迸发出又酸又甜果汁:树酝酿出了介于红酒与食醋之间的味道,尝起来似乎没有危险。我知道我应该等一等,但我吃了一颗又一颗。我不顾自己的手被扎刺刮伤,从荆冠上把果实剥落,我手上流出来的血比果实更红,果实沾染了我的血液,我觉得我在吃自己血肉。我向后仰倒,身体战栗发抖,昏睡了过去。直到深夜我醒过来,发现自己灵魂出了体壳,我的身体躺在哪儿,正在睡梦中,而我则离开了身体,神智清晰。梦里的我们,往往不再是原来的我们,一个男人在梦里变成了自己的兄弟,一个女人在梦里变成了国王,而梦中的他们并不以为怪。我心知自己正在梦中,并且变成了自己的影子。那一晚天上无月,暗云遮盖住星辰,但天光依然足够叫人投下阴影,将我变得比夜晚更暗黑。我就躺在自己身体的下面,蜷缩在弯曲的膝盖之间,平铺的衣裙之下,藏在我后颈的毛发下面。因为这是个梦,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从脚底开始慢慢渗回自己的体内,我在自己睡梦的身体上游动,把自己影子的碎片收集回来,慢慢拼凑成一个短小的自己。随着鼻息,站在了自己唇上。这就是火棘树,因为形似火把,也被叫做火把树,耐寒耐旱。果实酸甜,可以榨汁,果实可以榨油。md累死我了,其他的另外找个时间再科普吧= =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中世纪奇幻浪漫爱情故事《红发孤女与神血勇士》自译 原书名firethorn 序章 御林苑”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