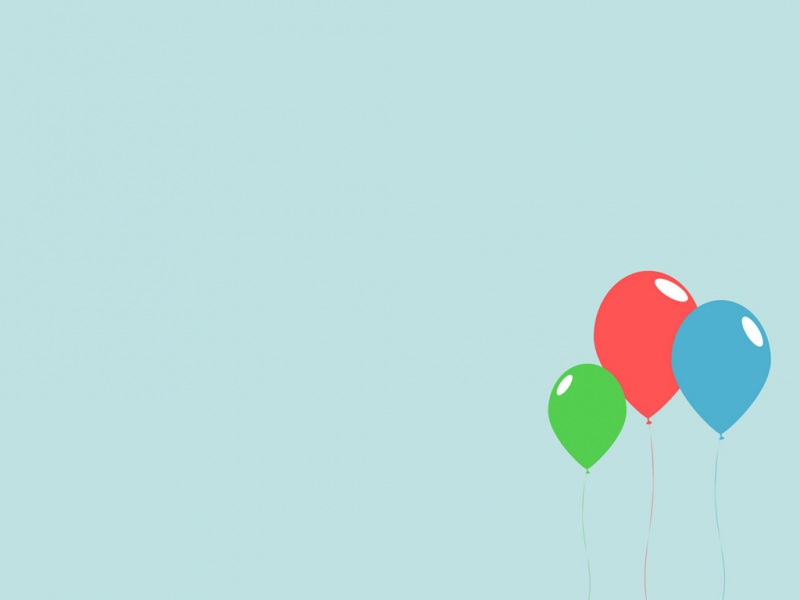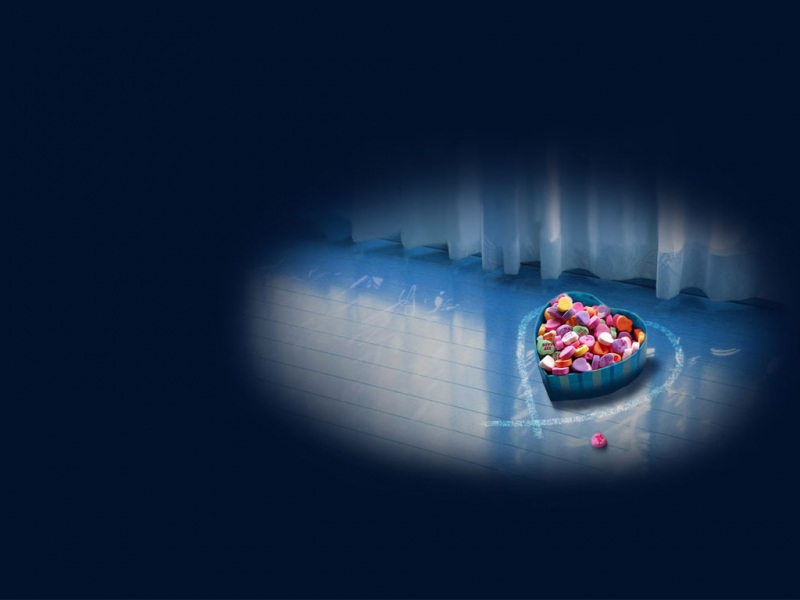提示:本文共有 7964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16 分钟。
2001年3月一个周六,在满满一屋子等待的孩子中,一个有著黑色长发、太妃糖般棕色皮肤的埃塞俄比亚小女孩说:「请帮我做一本关于我的故事的书……」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2001年,专精儿童参与式工作的克蕾契蒂展开一项计画。这项计画源于她和一群难民孩童相处,这些孩子从被内战和政变弄得四分五裂的非洲国家逃到约翰尼斯堡时,没有父母、朋友或家人在身边,逃难以及处在陌生、有时甚至充满敌意的收容国家,让他们出现心理创伤。克蕾契蒂带来许多二手旅行箱送给他们,每个孩子都选择了一个旅行箱,在旅行箱上画出自己的故事。 这些孩子用自己创作的图文,述说他们充满艰辛、渴望、力量和韧性的不凡历程。本书就是那些故事的集合…… 为什么是旅行箱?之所以选择旅行箱作为媒介,是因为旅行箱暗示与儿时记忆有关的强烈思乡要素、短暂的过客面向,以及隐含承诺。旅行箱有可以让每个人看到的表面,以及拥有者选择是否要公开的内部隐藏空间。 故事怎么说?这项计画约莫花了三年完成,纯属自发性质,孩子们可以选择要透露多少、是否想被录音,以及是否真的想说。克蕾契蒂誊写用录音机录下的故事,只针对顺序和可读性加以编辑,试著确实呈现孩子们的叙述,并保持口语的形式。写成之后,孩子们会仔细读过自己的故事,协议哪些部分可以发表、哪些部分他们不想被纳入书中,以及哪些部分需要变更以保持机密。 来听他们的故事…… 孩子们的哀伤、失落、经历的流离颠沛,令人震撼;他们的恢复力、安排计画的能力、苦中作乐从自身遭遇中找出趣味之处的能力,也让人感动不已。这些孩子不只是环境的受害者,也是幸存者。 打开这些旅行箱,看看里面,听听他们的故事…… 旅行箱的故事黑色大地上,十四个孩子,他们的旅行箱,和他们的故事The Suitcase Stories: Refugee Children Reclaim Their Identities作者:格琳妮丝?克蕾契蒂(Glynis Clacherty)、说旅行箱故事的人,及黛安?薇芙琳(Diane Welvering)译者:林丽冠出版:脸谱出版定价:360元出版日期:2009/06/02类别:传记作者简介:格琳妮丝?克蕾契蒂(Glynis Clacherty)研究员,专精儿童参与式工作。过去十年,她和非洲南部的孩子一起探讨HIV/AIDS、童工、虐童、贫穷和移民等问题,这项工作有绝大部分促使当局在制定新政策和新法时能够听到孩子们的意见。「旅行箱计画」是一项透过艺术计画实施的社会心理支持,克蕾契蒂在2001年和休布罗的难民儿童一起展开这项计画,休布罗是她认识孩子们的地方。本书将披露这些孩子的故事。 书摘请帮我做一本述说我故事的书 在约翰尼斯堡贫民区耶稣会难民服务机构办公室等待我的孩童,都是「落单或没人陪伴的孩子」——未满十八岁、在离开祖国或前往南非的路上变成孤儿或是与父母分开的孩子。塞娜许是其中一个。当孩子们用图象描绘出他们在约翰尼斯堡的生活,以及到达此地所经历的旅程时,塞娜许对我述说她的故事。 我以前在厄立特里亚上学,那是一所寄宿学校。我的父母住在埃塞俄比亚。我们有一栋很棒的房子。我们去过埃及,我很小的时候还去过意大利。 每次假日的时候,我都会回家看父母。那时我十二岁。有一天我发现他们不在家。我问一个朋友,我的父母到哪里去了。她说她不知道——我得回学校。后来我回到学校。老师说我不能再待在那里上学。我跑到肯尼亚边境。我请人从那里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旺雅。我告诉她,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在哪里。她叫我回学校。我在边境看到一个女孩,我在学校认识她的。她邀请我跟她一起去奈洛比。 我们在奈洛比待了一星期。后来我们去坦桑尼亚,接著又去三兰港(Dar es Salaam)。之后到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很糟糕。在监狱里,他们给我们吃很差的食物。我一直哭,因为一切变得不同又陌生。我的朋友,她在监狱染上疟疾。我觉得很不舒服。后来又去莫桑比克。莫桑比克的人很不好——很可怕。后来,我们在斯威士兰待了两天。 在南非边境,警察捉到我们。我一直跑——警察对空射了两枪。我还是在跑。有一个男孩付一些钱给警察——我不知道多少钱。 后来我跑到约翰尼斯堡。我住在一间公寓房间。在那个地方,我跟两个来自我的国家的女孩一起住。其中一个女孩,她把我丢在那里。她有事跑去开普敦,之后没有再回来,然后她打电话给另一个女孩,还跟她说她不会再回来了,我一直哭,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有个男人说我必须付一些钱当房租。但是我不知道要付多少钱。我在街上,我在哭,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哭?」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必须到邦提市(Ponte City),那个地方有个妈妈带我到那里〔耶稣会难民服务机构〕,那里有很多其它国家来的人。就在那里,我遇到米利安。1999年开始,我就和米利安一家人住。 如果我可以许一个愿,我希望读完书,然后回我的国家去找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不知道我在哪里,或者可能他们以为我已经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也许他们以为我死了。 那天下午我离开时,塞娜许跑来找我说:「请帮我做一本关于我的故事的书。人们需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自愿来这里的。他们需要知道。」 我整个星期都在想塞娜许和她的故事。我自己的女儿也是十四岁,也有一头黑色长发。我整个星期都在想,如果女儿有一天回家发现我们都被带走了,她会怎么做。她能够像塞娜许那样四处飘泊吗?这些特别的事件会对她造成什么冲击?我这个作母亲的如果不知道她的下落,会有什么感受?如果她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她会有什么感受? 到了周末,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再次和团体会面,协助塞娜许说出她的故事,就像她要求的一样。本书就是那些故事的集合…… 「打开这些旅行箱,看看里面,了解难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阿卡西欧的旅行箱(来自安哥拉) 「我的人生就像一个没有手把的旅行箱。旅行箱上这个人,他的生命不平衡,崎岖不平。他总是跌倒,需要再爬起来。就像我一样。」 阿卡西欧是所有孩子中最孤独的。他画了一幅悲伤的自画像,画著从脸颊流下的泪水时,我在一旁看着,当我再看的时候,眼泪已经被涂改掉了…… 阿卡西欧约九岁时,跟著他母亲和妹妹从安哥拉到南非。他母亲因为工作,把他托给一位安哥拉老太太照顾,回到安哥拉,一去不返。阿卡西欧没有和任何安哥拉的亲戚联系,与他非正式的监护人及妹妹很疏远。他独自住在约翰尼斯堡西郊。 我的人生就像一个没有手把的旅行箱 阿卡西欧是所有孩子中最孤独的。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十五岁,住在耶稣会难民服务机构的一间公寓,但是没有被安排接受公寓里的女监护人监护。他没有办法取得援助,除了耶稣会难民服务机构提供的住宿和学费之外,必须自谋生计。他独来独往,经常用他的魅力向仁慈的成年人取得食物和支持。他很少与其它孩子互动,偏好独自工作和走路。 他哪一项工作都做不久。刚开始的几个周六,他都在闲晃、打扰其它孩子、和我及黛安聊天。这种情况过了两周之后,我们认为该是鼓励他做一些事的时候,所以委婉地要求他开始作业。「我不知道该在这个旅行箱上做什么。我的生命里一无所有,没有东西可说。」他说道。「嗯,也许你应该想想,为什么你选择唯一一个没有手把的旅行箱。」他走开,做了一个简单的图案,小心地把它黏在旅行箱手把曾经所在的位置。 然后他画了一幅悲伤的自画像。他画著从脸颊流下的泪水时,我在一旁看着。当我再看的时候,眼泪已经被涂改掉了。只是到后来,当我开始比较了解他的时候,才了解这有多重要。阿卡西欧几乎没有让任何人看出他觉得自己多么孤独。他偏好「我不在乎,我可以应付,我是幸存者」的游戏。 在我的图画里,这个人身边发生了很多事。画里有血、黑色和黄色。他身边有好事和坏事——多半是坏事,比方说校园歧视。学校的同班同学,他们总是会说你的闲话。「你应该回你自己的国家!」诸如此类的话。他们不知道,我们绝不是自己选择来这里,那是因为某些原因,我们才会到这里,比方说我的国家的战争。「让我们自由」,我的旅行箱上写著。我们是流亡异国的难民,重点是,我们希望受到和南非人同样的待遇。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出生没有差别,因为我们都是非洲人,而且我们都是人类。旅行箱上面写著,应该对难民一视同仁。 这个在我的旅行箱这里的标语:「我的人生就像一个没有手把的旅行箱」,说出了更多关于图画中这个人的事。旅行箱上这个人,他的生命不平衡,它崎岖不平。他总是跌倒,需要再爬起来。就像我一样。 她一去不回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阿卡西欧的认识只有那样——他的人生崎岖不平又失衡,就像他没有手把的旧旅行箱。他很少谈他自己,偏好用他模仿得来的「酷炫」美式英文,以各种嘻哈态度和言词,广泛地谈论难民及在休布罗的生活。直到他离开耶稣会难民服务机构的公寓,被安置在普勒多利亚外的儿童之家时,才告诉我他的故事。 他九岁时跟著母亲和妹妹到约翰尼斯堡。他妈妈回安哥拉时,把他们托给一个在伊奥维的安哥拉老太太(他称她为祖母)一去不回。等他年龄稍长,变得较难相处,老太太把他赶走,而且禁止他去看他妹妹。他很少谈论自己的感情,以及被抛弃所带给他的感受,但是经常说他因为知道如何取得协助,才能够生存下去。他说故事的时候很谨慎,每次他显露任何悲伤的感觉,都会补充说他不是一直很伤心,或者说他反正会生存下去——他从不让我们任何人看到任何软弱的地方,或者他可能太害怕让自己的悲伤显露出来。 以下是他告诉我他待在社服单位时的情况。 我待在公寓一年。后来公寓在12月就要卖给别人。所以我必须离开公寓到一个儿童之家。我不知道我会去哪里。那就像过一天算一天,前途茫茫的生活。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命里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要在11月28日搬出去。到了27日,我还不知道要去哪里。我到耶稣会难民服务机构叫我去的政府社工那里。我到办公室问那位社工,她根本不知道我该去哪里。她说儿童之家满了,爆满!她还告诉我,我明天就得来报到。她一直跟我说那样。我有点害怕,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觉得害怕,因为有人关心我。 后来到了周五,我回去那里,她带我到街童之家——喔!助理社工带我去。我真的不喜欢那个地方。我跟助理社工一起走,我的感觉是:「我觉得我没办法待下来。」那里很暗,里头的人很怪——他们是街童。我对自己说,公寓还有几晚是空的,我有钥匙。我对自己说,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我回到公寓,晚上在那里睡。那里只剩我一个人,我有钥匙。我真的是孤独一人,但是我有收音机作伴,音乐——还有我的书——帮助我觉得坚强。 隔天我来这里做一些艺术作品,然后去找我认识的天主教女士,因为周末时公寓会被接管,如果我在那里,他们会把我赶走。我周末在天主教女士那里睡,周一她把我带到社工那里。你帮我在伯诺尼找到地方。 我第一次到那里,就觉得好像监狱——我觉得我的梦想被粉碎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已经终止。那是我的感觉我看不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离开之前,我跟你说话,你说我是讨人喜欢的人,所以我不会有问题。那种话鼓励了我,让我有一点信心,相信我会没事。我幸存下来。然后假期过后,他们告诉我,我不符合他们的标准——他们说那里是为街童设置的。我觉得那不合理——我是没有父母的孩子,而且我必须离开公寓——如果不让我住,我不管怎样都会流浪街头。但是总之……后来1月的时候,社工带我到普勒多利亚的沙桑谷维。 我从黄金城市买了这个电颤琴 那是一条漫长的路,在路上,我想到我的朋友、我的妹妹和约翰尼斯堡。约翰尼斯堡是我的朋友、我的一切和每个人在的地方。要离开那里真的很难。我要去普勒多利亚了。最后我到了那里,到达那个很远、遥远的地方,沙桑谷维。当我们进去那里的时候,那里就像一个指定的地方,那是我该去的地方。我必须待在那里一阵子,体验一下。但是我真的不喜欢那里,那里很平淡无聊,我觉得我在那里不再有任何希望。我被安排住进跟其它孩子在一起的宿舍。大部分的人说祖鲁语和索托语(Sotho),不说英语。有时候他们觉得低我一等,因为我说英语,但是不是这样,我只是在说一种语言。那只是一种语言,如果我说得比你好,不表示我比较优秀。但是他们有时候好像有点嫉妒我。不过我幸存下来。我在那个地方幸存下来。我做到了。有时候我想到自杀,但是我做到了。 那里没有太多事发生——我唯一拥有的东西是我的音乐。我到那里的时候,我买了这个电颤琴「我来自黄金城市约翰尼斯堡」,后来我的收音机坏掉,这些都消失了。他们有个人弄坏它,因为他们嫉妒。我不觉得难过——我总是表现出毫不在意的态度。我知道我有一些关心我的人,所以我其实不在乎那些不想当我朋友的人。你就在我附近,而且你来看我。 某个周六,我和另一个孩子拿著录音机坐在树下的时候,阿卡西欧大步慢跑过来跟我打招呼:「最近怎么样?」我以为他已经逃跑,而且准备好接下来要怎么做。他告诉我,他被安置在贝兹谷地一个非正式寄养妈妈那里,因为他太大了,不适合住在儿童之家。 最后我怎么会在这里,事情是这样的。他们说我现在十八岁,我不应该待在儿童之家。 当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年龄——跟我一起住的祖母不确定我的年龄。我妈妈离开的时候,没有留下我的出生证明。她没有留下我们的身分文件和资料,所以我其实不知道我的年龄。在学校的时候,我知道生日月分和日期,但是搞不太清楚是哪一年。我妈妈在1996年离开,我想那时我大概十或十二岁。所以我去儿童之家的时候,我找过医生。他说我十八岁。后来他们说我太大了,不适合住在儿童之家,所以我的社工安排我到一个寄养妈妈家,离开那里真是让我松了一口气。我终于熬过来,我离开了。我很高兴。我的养母,嘘!我跟你发誓我说的是真的——她很严苛,也很挑剔——我知道那有时候是正常的,我存活下来了,但有时候我真的不喜欢她说的话。她经常咒骂、生气——让人觉得有压力。她拿不到给我的任何钱——她把气出在我们身上——骂三字经——那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但是那里比儿童之家好,而且我幸存下来了。 有一天我会回家 阿卡西欧继续幸存下来。他离开养母,仰赖他人的慷慨过活。2004年底,他再度被捕,被送到林德拉。这次我们担心他被驱逐出境,因为安哥拉人不能再申请难民身分。透过人权律师的协助,他根据他大半生都住在南非这项事实申请永久居留,但这个程序可能长达两、三年。他和安哥拉那边毫无联系,要取得安哥拉护照也很困难,因为他不能证明他是安哥拉人。他无法找到正式的工作,没有人想雇用没有身分证件的年轻人。他真的没有身分,谈到家人及真正的他时,他所表达的东西就是身分。 我想到我妈妈——我们从来没有真正了解对方。我觉得我现在长大了,她却从来没有在身边。我想跟某个人说话,某个会了解我、像我妈妈一样的人。但是她不在,她从来没有在身边。我已经失去了她。那真的很悲哀。我觉得我的生命中失去了某种东西——更明确地说,失去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一直很命苦。我们所有的人都分散了。在某方面,我需要我的家人,但是我没办法跟他们联系。那真痛苦。 当我小时候,我妈妈,当她还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她告诉我,我的名字是我爸爸帮我取的。他用他最好的朋友的名字来帮我取名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非洲名字,不过我有葡萄牙名字。我对我从哪里来的很好奇,所以有一次我问我妈妈。她告诉我,我必须遵照我爸爸的文化。她告诉我他做什么工作,但是我已经忘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时我还小,她还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对一部分的我并不了解。我现在所属的文化不明,只是「住在南非、认识新朋友的阿卡西欧」。我的文化是未知的。我只是适应现在的文化罢了。 也许现在我太疏忽,我甚至没有想过我的文化。也许我必须把它找出来。因为如果有一天我必须回到安哥拉,他们会问我,我来自哪里,我会不知道…… 有一天我会回家。 对叙事过程的反思格林妮丝.克雷彻提 在团体开始定期聚会后不久,我向大家提起,塞娜许要求制作一本关于她故事的事,我问他们是否想要这么做,每个人都同意,所以我每周六都带著我的录音机。这些孩子一直学著在社会上尽可能保持低调,我知道编一本书会是让他们在这种社会中引人注目的重要方式,我了解一本书会是建立他们身分和自我价值意识的重要方法,我也知道叙事具有治疗效果。我和利用叙事疗法的临床心理学家合作多年,知道这是一项强大的治疗工具,所以我鼓励将说故事当作流程的一部分。 当他们完成旅行箱或地图的整体艺术创作时,我邀请他们带著自己的艺术作品前来,告诉我关于他们的故事。当其它人在学校方院附近的艺术教室工作时,我和受访者经常坐在方院树下交谈,有时候他们会成对或是成群前来(通常是一群朋友),有时候是只身前来,如果是成群前来,其它人会静静聆听,见证故事。他们可以选择要不要和我谈话,有很长一段时间,某些孩子并没有前来叙述故事,事实上,有一个孩子从未述说她的故事。他们经常选择单独和我谈话,特别是如果故事内容很惨痛。我总是让他们选择是否要关掉录音机,但是他们很少要求这样做。就好像录音这个动作让说故事更具重要性。 叙事方法根植于麦可.怀特的叙事疗法,怀特是这个领域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说,治疗师应该协助人们叙述「密集的故事」(thick stories),并且藉著为他们制造叙述和重述故事的机会,看看他们拥有哪些知识和技能。在叙述和重述故事的过程中,人们开始看到,起初看起来像创伤事件(他们是其中的受害者)的消极描述,其实是他们如何运用特定策略以求生存的描述。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故事会变成多个故事,而且是幸存和创伤的描述。 在旅行箱计画的艺术作品中使用多个层次,是这个想法的具体表现。透过艺术作品,孩子们创造了「密集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他们所扮演的不只是「难民」。透过叙述自己的艺术作品,他们也开始看到他们的故事充满了知识和技能,而且他们并未因此受困和瘫痪。本书所包含的许多故事中,这种「新故事」的收获非常显著。 孩子们确认叙事在疗伤止痛上的价值。 一定要把问题说出来,因为把问题放在心里既没有办法解决事情,也会让你生气,但是当你把它说出来,你会觉得比较好。 他们把一项事实看得很重要:他们从未被迫说出他们的故事。团体成员每周六会和接受过传统心理创伤疗法训练的辅导员谈话,这是他们必须谈论这个经验的场合。告诉塞娜许我等著把她的故事放进书里 那为什么塞娜许的旅行箱和故事没有放进本书?她的遭遇正好可以做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如果这些孩子没有得到足够的援助,他们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 塞娜许极度独立,因此安然度过艰辛的旅程,但是这种精神让她很快就和她非正式的养母起冲突。她后来离开庇护所,和另外三个年轻的埃塞俄比亚女人同住,她住后面的房间,睡在地板的垫子上。她离开庇护所之后,我继续和她联系,每周六我会去接她。学校生活变得令人沮丧,因为她的英文不大好,她被安排在学生年龄比她小很多的班级里。她上一所技术学院一段时间,但是她变得消沈,她很需要父母持续无条件的支持,就像许多十来岁的少女所企求的一样。她消失了。她没有回到学校考试,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耶稣会难民服务机构的社工将她列为失踪人口,但是有谁会在乎一个年轻的外国人失踪? 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她说她没事,但是她待的地方不太好,她需要协助。我原本安排要在镇上和她碰面,但是她没有出现。我继续在我拥有的不同号码手机里留下讯息,我的留言永远是:「我不会生气;我不准备批评你所做的任何事——只要回来和我谈谈,让我确定你安全就好。」 某个周末,艾吉说她看到塞娜许,塞娜许现在和一个男朋友同居,那个男人年纪比较大,情况不好。但是艾吉不肯跟我说她在哪里,我便传送另一则简讯:「告诉塞娜许,我们正在写我们的书,我们需要把她的故事放进来。」 艾吉跑去找她的时候,她已经搬走……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开卷严选:旅行箱的故事”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